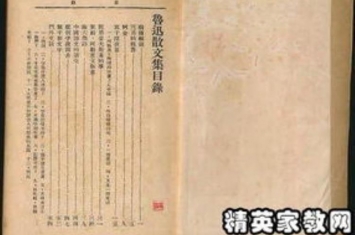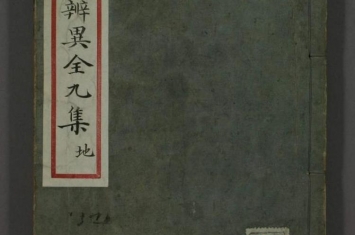栏目:文棚
榆钱(散文)——“关中三味”之一
桃花慢绽时,眼帘便渐日呈现出草润树艳的纷繁来。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可人心绪的草木青,招惹馋虫的绿春芽。村头庭院、野旷田畦,都着洋溢着一树一树的芬芳。一街两巷,也铺展出鲜嫩的春菜诱惑味蕾的缤纷。

手指划过这个季节的屏幕,顽皮的表妹通过微信,将我千里之外最富生机最富滋味的故乡——关中平原本真的风物,点发到我的眼前。于是,一帧帧的图片轻染黄尘,愈发地素朴、鲜活:晨曦中的香椿在院门口一侧油绿油绿,鸿门塬上的榆树站成一绺,初生的榆钱就晶莹剔透了。它们,都以灵动的姿势站满心扉,定格,更清晰;摇曳,却模糊。发小说,刚子,回来尝尝鲜,还是给你寄过去?那一刻,我不觉喉结一转,咽下味蕾条件反射后渗出的津液。
乡愁最稠数暮春,春色怜魂最易衰!
一晃,离乡已近三十载。每逢南方三四月,源自灵魂的自觉便会将记忆拉向遥远的关中平原。最为敏感长情的味蕾不会欺骗自己,因为无论游子走到哪里,只有味蕾能够更加紧牵与生俱来的家乡美食的滋味。于我,最本真的家乡味道源出梢头的芬芳,最浓酽的乡愁莫过于味蕾上的“关中三味”:榆钱、槐花和香椿。
我对榆钱的原味与加工成菜肴的记忆至今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种记忆之所以能够保鲜如初且一直清新,关键在于它能将快乐与幸福持续发酵。
在老家,榆树不像杨、柳、松、柏和泡桐那样,生长在宽敞扎眼的旷野、山坡,成材后或作撑构屋厦的椽、檩 、栋、梁,或伫立水畔旖旎成景,或作肉砧案板寿木棺材。常处贫瘠缺水的僻隅,少人问津的榆树,皮糙质粗纹理散乱,枝枯干死后,宿命难免归于灶膛。榆树的面相材质诚然不敢恭维,因而诸如肤似榆皮、榆木脑袋等不雅的比喻都将榆树顺了进来。但听了奶奶辈的老人一番说叨,又怎不令人对榆树刮目相看——榆叶、榆钱,纵使榆树皮,都是青黄不接甚至饥馑年景下灾民果腹活命的最后保障。一棵棵粗卑、孤独的榆树,一眨眼成了人们趋之若鹜门庭若市的救命树!叶子被摘光了,榆钱被捋完了,就连粗糙苦涩的皮质也被铲刮得精光!最后,将自己的枝柯、躯干一道融入熊熊的灶火,用自己的性命救千百万生灵的性命!那时,谁又敢否认榆树贵如金呢?
桃花初绽草芽探头的时候,鸿门塬上的榆树上就会挂起一串串榆钱,金灿灿地悬垂着。风吹过,枝条托举着金黄、密匝的榆钱,舒缓地曼舞出妩媚。
我的少年虽不至于闹年馑,但也确是一个食物很不丰富的时代,不少家庭一年总会出现短粮断顿的情形。七八岁的我亲见大人们夹着空袋早出晚归,从亲戚家借回一袋半袋玉米面、红薯或者面粉,哺养一堆处于半饥不饱状态的孩子,艰难地度过一天又一天。可能是我家孩子少劳力多的缘故,记得父亲只借过一次粮食。那时的我们,都是野生放养的。大人们都在生产队忙农活,尤其夏忙、秋收时节,他们匆忙简单地煮一顿没有几滴油星的汤面、糊糊,我们就算被打发了。这也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无羁飞翔的机会。早饭午饭没有太多内容,晚饭还没到点肚子就开始咕咕地抗议。弟弟、妹妹们只知道肚子空了,要吃的,我们这群七八岁上下的大孩子便自力更生起来。
榆钱是榆树的花,也叫榆钱荚。状似圆形方孔铜钱币,肉薄如纸,周身灿灿,中间微凸。一枚枚榆钱缀枝成串,折枝下来,捋一把榆钱入口大嚼,脆、甜、鲜,肚子慢慢便充实而满足。行文到这里,弟弟妹妹们嘴巴粘着榆钱碎片一脸漾笑手舞足蹈的小样不禁浮现脑海。幸福夹杂着酸涩的时候,眼睛难免被搅得一片迷蒙。

大人们挣工分了,我们便呼朋引伴直奔当年项羽和刘邦分道扬镳的鸿门宴所在的鸿门塬。春雨涮过,晨曦一扫,不怎么粘脚的塬畔上,榆树神清气爽地一绺儿排开,满枝金光闪烁。仰头近看,低处的榆钱已被人折走。我们只有爬上榆树采折。我是个喜欢登高爬低的主,胆大、敏捷。所以,伙伴们总喜欢跟我一起玩,关键是每次都有收获,都能解馋。
黑蛋哥怂恿道,你人小,利索,你上,我在下面看着。弟弟妹妹们也在吆喝鼓动。我袖子一挽,为了防滑又吥吥两声在左右手心吐了些唾沫,纵身跃起,双上抱紧树干,两腿一夹,上下一登,轮番换手上攀,几下子就坐到了树杈上。当然,爬树是跟我那长我几岁的三叔学的。
早春的风还是有些料峭,这棵榆树不算粗,但有一丈二三尺高,起身站定,人和树枝都在摇摇晃晃。我强大着胆子左手把住粗枝,伸出右手折断榆钱枝条。随着一串串榆钱擦着春日的阳光翩然落地,伙伴们争抢入筐的嬉闹,身边榆钱的逐渐稀落,我将脚步横着挪向远处的弯曲的树枝。筐里的榆钱已经漫平筐沿。黑蛋哥仰着脖子叫嚷,差不多了,折完那串就回!反复伸动右臂,加上来回折弄,我的手脚有些发软,但还是努了把力,用渗出汗水的手勾住了那根榆钱条,折啊扭啊,忽然脚底一滑,侧身便往下掉。情急中,我双手抓住了几近折断的枝柯,悬在空中。下面,黑蛋哥和几个弟弟手挽成一圈,立刻围拢过来。松手,跳,咚地一声,他们几个做了我的肉垫。起身的时候,他们个个呲牙咧嘴地揉着屁股。只有庄娃指着我“嘿嘿嘿”地猛笑:裤裆扯开啦!快看,屁股蛋子露出来了。
趁大人还没放工,我一手捏住开裆处,一溜烟跑回家换了裤子。黑娃哥指挥大家分工负责,各自从家里偷来油、盐、酱、醋、辣椒面,找个没人的深土壕围成一圈,烤熟红薯,一人盛一碗凉拌榆钱,个个吃得满嘴的榆钱碎末。
第二天,我、黑蛋和庄娃都被家长掌了屁股。因为,我弄破了裤子,他们偷了家里的菜籽油和酱油。一晃快四十年了,他们都成了爷爷,可第一次炮制脆、香、酸、辣、爽的凉拌榆钱还一直挂在我的味蕾。每每见面,挨打的旧事总会成为最开胃的下酒菜。
上小学以后已是八十年代,日子慢慢好了,我们几番琢磨,竟把榆钱捣鼓出了几样美味的菜肴:油泼辣椒拌榆钱、榆钱炒豆腐、榆钱鸡蛋汤、榆钱蒸麦饭等。
乡情的春秋轮回了二十年。再回首,我才真正了解了长在乡愁里的榆钱。
翻开《本草纲目》,上载:“榆未生叶时,枝条间生榆荚,形状似钱小而成串,俗呼榆钱。”
等到看了清代张潮编纂的《昭代丛书》,其中的《人海记》竟有“时官厨采供御膳”的记载!没成想,这最土的榆钱儿原来还是入得朝堂官厨,供皇帝老儿尝鲜的稀罕菜品。
大概出于这个缘故,文人墨客的笔下亦不乏对榆钱的青睐、咏叹。唐朝的边塞诗人岑参在他有些落寞的当儿如是慨叹:“道旁榆叶青似钱,摘来洁酒君肯否?” 北宋文学家欧阳酒足饭饱之际喜吟道:“杯盘汤粥春风冷,池馆榆钱夜雨新。”元曲也有民间嬉戏调侃之曲:“又不颠,又不仙,拾得榆钱当酒钱。”

前年春出差北京,老同学还真让我在一家农家菜馆长了见识。细瞧菜单,什么榆钱炒肉片、榆钱炒鸡蛋、鸡蛋琉璃榆钱、榆钱面托、焦炸榆钱丸子,什么拔丝榆金珠糖醋熘榆金珠、榆钱烩豆腐,点心有金星榆钱糕、切边三鲜榆钱饼,汤有榆钱蛋汤,榆钱豆腐汤……凉菜、炒菜,主食、汤品,那真叫一个齐全!
由此我就忖思,不管是秦汉,还是唐宋元明清,也不论长安、汴梁,或者洛阳、北京,凡是栽种榆树的地方自然少不了榆钱这品类不一的民间家常菜食。尔后,经过御厨匠心独运,将榆钱加工为皇宫的奢侈菜肴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岭南到北京,第一次品尝到如此丰美的榆钱佳肴!那是北京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但每一道菜都氤氲着泥土和榆钱本色的芳香。
再次徜徉故乡关中这块中国历史转弯的地方,多少传诸汗青的传奇在此上演!周幽王戏褒姒引发春秋争霸,秦始皇长睡不醒处兵马俑赫然面世,鸿门宴刘项分野天下归汉,华清宫缠绵悱恻长恨歌仍然袅袅,“西安事变”国共联手促成全民抗日……
但于我,无论牧风而行有多远,榆钱这种关中树菜的味道从未走出我的舌苔、味蕾……
(文棚是一个以散文为主的共享平台,面向全球华人开放,供作者、读者转发推送。其“写手”栏目向全国征集好稿,外地来稿不论公开发表与否,皆有可能采用。凡当月阅读量达6500次,编辑部打赏100元/篇。请一稿一投。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非签约作家请注明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全称、账号。)
◆中山日报报业集团新媒体中心
◆编辑:徐向东
◆二审:蓝运良
◆三审:岳才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