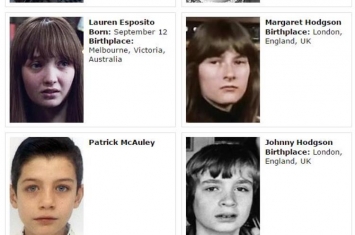——用中国智慧解开生命起源与人类起源之谜
作者:张宝盈
(本书已由华龄出版社于2020年10月出版发行,书名《探索自然之谜全三册·中册·生命起源》)
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接上篇)
第十章创生于山岛成野人
大自然创生生命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束缚的。无论怎样“奇异”的生命都可能被创造出来。这就导致了生命现象的复杂性,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目前有关生命起源的理论还无法解释所有的生命现象,尤其不能解释一些带有奇异色彩的生命现象和物种,这就使得这一理论的拥趸者对不同观点具有很强的“排斥欲”和“剔除欲”,一见到有违他们的理论的生命现象和生物物种诸如野人、水怪等,便会矢口否认,指为虚妄。他们惯于采用双重标准,对于不符合他们理论的生物物种,往往要求提供过分苛刻的证据,似乎只有他们本人亲手捉到一个活体才能算作“可靠证据”。而对貌似符合他们的理论的“证据”的要求又宽松得没有边际,仅仅一个牙齿化石,一个头盖骨化石这样信息量十分有限,且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实物,也被他们宣称为“可靠证据”。既然“猿人”的一个牙齿,一个头盖骨都可以作为“证据”,为什么野人的毛发、粪便、足迹、影像等不可以作为证据?然而理论的弱点掩盖不了事物的真相,仅靠否认、抹杀事实是无益的,必须正视和敢于面对这些现象,才能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完美的生命起源理论。


一、“家人”曾经是野人
时至今日,有关“野人”、“水怪”被发现、被目击的报道,仍不时见诸荧屏、网络、报端。虽然在一些故作正经的生物学家眼里,它们都是“没有确凿证据”的虚构的生物而不予置理,但仍然有一批具有理性思维的生物学家肯定它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相信,数以万计的古今中外的目击观察、实物证据不可能全部做假。
历史文献向我们展示的是,当地球具备了创生生命的功能以后,它便“肆无忌惮”地“粗制滥造”起来。创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奇异生命种类之多,品目之繁,令人瞠目结舌。
大自然创生了“家人”,还“突发奇想”地创造了不少野人。其实细细想来,天地造人之初,或从天降,或从地出,其时既无衣被,复无庐舍,亦无粮草,落魄荒野,自不免茹毛饮血,生食橡栗,何尝不也是十足的“野人”?尤其是那个“初来乍到”的“第一人”,虽然抢得了个“天下第一人”的美名,生活状况却实在惨兮兮。只是后来出了些“圣人”或“神祇”,“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有巢氏教人构巢,后来人发明了织布的方法,这才慢慢由“野人”变成了“家人”。“野人”的存在,无足怪也。因为“上天”老是在不停的造人,如果它把一个“人”或类人的动物创生在了山野之间,他就只能选择做野人了。
对于进化论来说,野人、水怪、异形、怪兽、龙凤……无异于噪音、累赘、噩梦,因为这些东西越多,用进化论解释起来越困难。实在太给进化论“添乱”“添堵”了。进化论最适于解释规则、平滑、均衡、渐进式、线性的、无差别的生物演化,不喜欢差异,因为差异越多,越难以用“环境变化”来解释。所以对于奇异生物,进化论是要极力回避、排斥的。进化论厌恶差异,大自然却钟爱差异,创造出了无数的平常的和奇异的物种,野人也是其中之一。
20世纪70年代,相关科研机构已组织过相当规模的野人考查,其间虽未找到野人活体或尸体,却发现不少诸如野人毛发、粪便、脚印等间接证据,但部分学者对这些间接证据仍持质疑态度,他们对野人的存在是基本否定的。
其实这些毛发、粪便、脚印之类,即使拿到法院打官司,也可以依法认定为“物证”的,不过我们的“科学研究”的“规则”似乎比举世公认的“法条”还严格。
数以千计、万计的目击报告不算数,毛发、粪便、脚印不算数,那还是“科学”吗?
既然出土的生物化石可以作为证据,一半个牙齿、头盖骨都被称为“铁证”,那么野人的毛发、粪便、脚印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证据?
事实是以真实存在为根基的,与承不承认无关。试图以“拒不承认”否认事实的存在是徒劳的、可笑的,也是无益的。
其实有家狗就有野狗,有家猪就有野猪,有家马、家羊就有野马、野羊;有家鸡、家鸭,就有野鸡(山鸡)、野鸭,……就“家人”就有“野人”,自然之理。“家人”不是野人驯化而成的,家狗也不是野狗驯化而成的。各有其类而已。
古今中外都有大量有关“野人”、“雪人”的记载,有关目击、捕获、打死野人的报道也是汗牛充栋。这些野人常常也是突然出现,且往往是孤身一人。所以野人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数千年来已有大量的观察记录,足可凭信。
现代出版的有关野人的书籍也已林林总总,蔚为可观。亦有部分照片、影像资料,以及活捉、打死野人的记录。种种证据表明,野人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
事实上,记载表明,许多“蛮族”在其创生早期,尚未开化之时,也具备某些“野人”特征。
《古今怪异集成》载,台湾土人,不知所自昉,俗谓之番人。闻自海外迁来,及宋末零丁洋师败,遁归。其种类甚多,南自加六堂至崇爻七十二社,北自崇爻至鸡笼番社,尤不可胜数。内山有社,曰嘟啯,其人翦发、突睛、大耳,状甚恶,足指楂(木 了)如鸡爪,升树如猿猕,善射好杀,俗称之曰鸡距番。食息皆在树间,非种植不至平地。深夜辄独出,至海滨取水,遇土番,往往窃其首去,土番亦追杀不遗余力。盖其足趾楂(木 了),不利平地,多为土番追及。既登树,则穿林度棘,不可复制矣。
这种似人似兽的“鸡距番”,近乎为“野人”矣。
出于南宋时期的《溪蛮丛笑》载:“犵狫蛮之尤怪者,两目直生,恶青衣人,遇之则有祸。去麻阳百余里,不常见。”
“两目直生”应该就是所谓“纵目人”。
《滇海虞衡志》卷十三《志蛮》记述了清时西南诸少数民族概况。其间有数十个肤色、语言、服饰、风俗等等大相径庭的民族。
其有相对落后的民族,与“野人”相去无几。如(犭 求)人,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无屋宇,居山岩中。
大猓黑,黑陋愚蠢,所食荍稗,即为上品。其余树皮野菜藤蔓,及蛇虫蜂蚁蝉鼠禽鸟,遇之生噉。不葺庐舍。野处与野人同。同类小猓黑,其习与同,但形状差小耳。
野人,露宿树巅,赤发黄睛,衣树皮,毛布掩其脐下。首带骨圈,插鸡尾,缠红藤,执勾刀大刃,采捕禽兽,茹毛饮血,食蛇鼠。性至凶悍,登高涉险如飞。逢人即杀,掠人暴于岩石上,或缚而鬻之。
可见,在现今已成为一大“自然之谜”的野人,在那时不过是“蛮”之一种。
在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只有10余人的小部落。他们皮肤是棕红色,头发卷曲,不论男女一概都赤身裸体。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语言都似鸟叫一般。
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和马来半岛上,有一个脸型像狗的民族,称为“狗面族”,他们的身材也十分矮小,一般不超过1.5米,男女几乎全裸着身体。他们会使用弓箭狩猎,并采集野果、蜂蜜。[1]
这些“怪异”的民族,无疑也都是各自独立起源,有各自独立的始祖、族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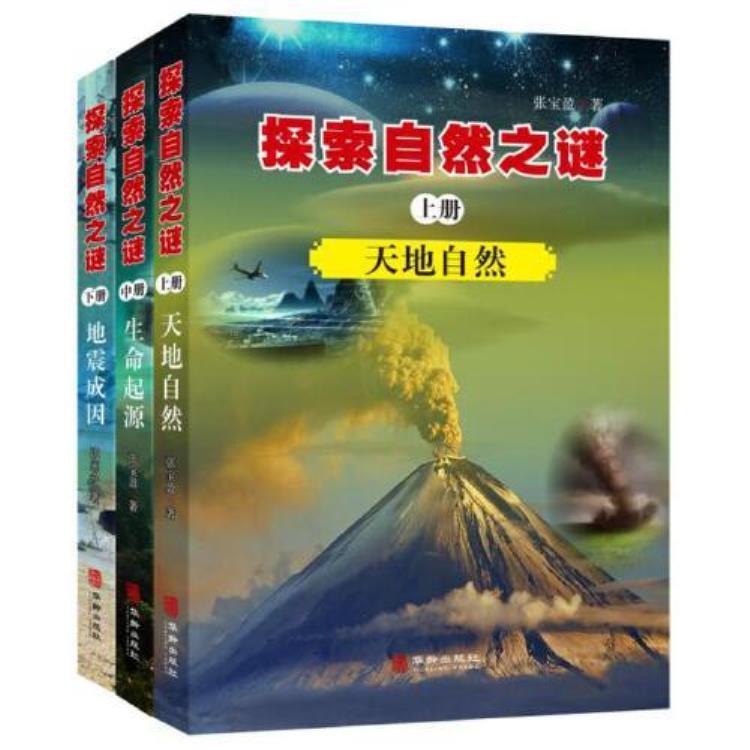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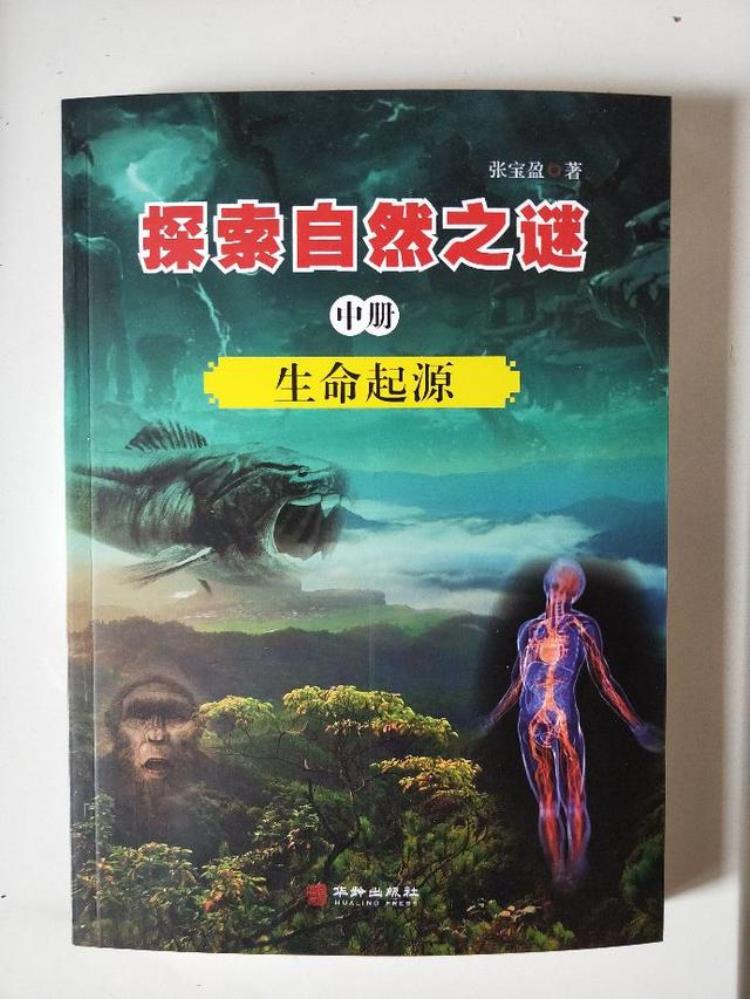
野人也是天地创生的万千物种之一,它们也许只是外形接近人类,实质上可能属于一种动物——介于人和猿猴之间的一种类人动物。
根据古今中外的文献记载,野人的种类有很多,就像任何一个物种都有很多的种类一样。它们中间也不存在彼此“进化”或退化的关系。此类就是此类,彼类就是彼类,它们从被创生开始就一直如此。
在历史文献中,对野人的记载,自古及今,两千余年,绵绵不绝。
《山海经》中即已广有记述。《海内南经》载:枭阳国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则笑,左手操管。……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
陈藏器《本草拾遗》:狒狒出西南夷……宋建武中,獠人进雌雄二头。帝问土人丁銮,銮曰:其面似人红赤色,毛似猕猴,有尾;能人言,如鸟声,善知生死,力负千钧,反踵,无膝……发极长,可为头被……帝乃命工图之。
罗愿《尔雅翼》载述“猩猩”云:“其状皆如人,与狒狒不甚相远……今人谓之野人,然而不知礼,故曰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在《兽部·寓类》亦有“猩猩”“狒狒”之载述,并引用《方舆图志》的记载:“狒狒,西蜀及处州(今浙江丽水县东南)山中亦有之,呼为人熊,人亦食其掌,剥其皮。闵中沙县幼山有之,长丈余,逢人则笑,呼为‘山大人’,或曰野人及山魈也。”又邓显明《南康记》云:“山都形如昆仑人……通体生毛,见人辄闭目,开口如笑,好在深山涧中翻石觅蟹食之。”
刘义庆《幽明录》云∶东昌县山岩间有物如人,长四五尺,裸身被发,发长五六寸,能作呼啸声,不见其形。每从涧中发石取虾、蟹,就火炙食。
《睽车志》卷四:蜀道多山鬼。有小吏暮行,见道旁一妇人立溪侧,小吏就丐饮且挑狎之,扪其胸臆间,皆青毛数寸,吏惊呼而走,妇人大笑,徐步而去。
《玄中记》云∶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伏。
《抱朴子》云∶山精形如小儿,独足向后。夜喜犯人,其名曰魈,呼其名则不能犯人。
《白泽图》云∶山之精,状如鼓,色赤,一足而行,名曰夔,呼之可使取虎豹。
《海录杂事》云∶岭南有物,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能夜叩人门求物也。
《述异记》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色赤目,发黄披身。于深山树中作窠,窠形为卵而坚,长三尺许,内甚泽,五色鲜明。二枚沓之,中央相连。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开口如规,体质虚轻,颇似木筒,中央以鸟毛为褥。此神能变化隐形,猝睹其状,盖木客山(犭参)之类也。
邓清明《南康记》曰,木客头面语声,亦不全异人,但手脚爪如钩利。高岩绝岭,然后居之。能斫榜,索著树上聚之。
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七载:“邕宜以西,南丹诸蛮皆居穷崖绝谷间,有兽名野婆,黄发椎髻,跣足裸形,俨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飞猱。自腰以下,有皮纍垂盖膝,若犊鼻。力敌数壮夫,喜盗人子女……其群皆雌,无匹偶,每遇男子,必负去求合。”
近代史志中的有关记载也不鲜见。
乾隆《南召县志》:洪武间南召西百叁拾里有野人,红发赤面,毛长尺余,饮泉食虫,见人大笑而避入于山。因名其山曰野人垜。
同治《续修永定县志》:元帝承圣元年十二月,天门山获野人,三日死。
唐朝李延寿《南史·梁武帝本纪》写道:“戊午,鲁山城主孙祖降,己未夜,郢城(今湖北省江陵县)有数百毛人,逾堞(偷爬过城墙)且泣,因投黄鹄矶……”
《纪闻》载,新罗国,东南与日本邻,东与长人国接。长人身三丈,锯牙钩爪,不火食,逐禽兽而食之,时亦食人。裸其躯,黑毛覆之。
此“长人”应即所谓野人,号称长人国,则其国皆野人也,长人国今已不存,疆土亦无,想已沉入大海无疑。
《萍州可谈》卷二载,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鬈而黄,有牝牡,生海外诸山中。……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
这种近似黑人的“野人”虽然并非来自非洲的黑种人,而是“生海外诸山中”。说明在相对较近的海岛中,也曾有过这种近似黑人的野人存在过。
《新辑搜神后记》卷一载,晋孝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尝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见一人,身长一丈,通体皆毛。从山北来,精见之,大怖,毛人径牵其臂,将至山曲,示以大丛茗处,放之便去。
这是一个颇有善意的野人,极聪慧且善解人意,很有点“助人为乐”的精神。
《职方外纪·墨是哥》载,其中有一大山,山谷野人最勇猛,一可当百,善走如飞,马不能及。又善射,人发一矢,彼发三矢矣,百发百中。
这样“善走如飞,马不能及”的独特的野人是自然也是其地自生,是有它独立的始祖、族源的。
《搜神记》卷十二载,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国”,一名马化,或曰玃猿。
《新齐谐》卷七《大毛人攫女》载,陕西咸宁县乡间有赵氏妇,年二十余,洁白有姿,盛夏月夜,裸而野溺,久不返。其夫闻墙瓦飒拉声,疑而出视,见妇赤身爬据墙上,两脚在墙外,两手悬墙内,急前扶之。妇不能声,启其口,出泥数块,始能言,曰:“我出户溺,方解裤,见墙外有一大毛人,目光闪闪,以手招我。我急走,毛人自墙外伸巨手提我髻至墙头,以泥塞我口,将拖出墙。我两手据墙挣住,今力竭矣,幸速相救。”赵探头外视,果有大毛人,似猴非猴,蹲墙下,双手持妇脚不放。
这个类人的毛人生物,专挑有姿色的妇女袭击,懂得用泥块堵住人嘴,具有相当的智力,是一种野生的类人生物,也当属野人之例。
《子不语》中也有几则野人的记载:
卷二:关东人许善根,以掘人参为业。故事:掘参者须黑夜往掘。许夜行劳倦,宿沙上。及醒,其身为一长人所抱,身长二丈许,遍体红毛。以左手抚许之身,又以许身摩擦其毛,如玩珠玉者。然每一摩抚,则狂笑不止。
卷六:《秦毛人》:湖广郧阳房县有房山,高险幽远。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长丈余,遍体生毛,往往出山食人鸡犬,拒之者,必遭攫搏。
卷十八:《黑苗洞》:湖北房县,在万山之中。西北八百里,皆丛山怪岭,苗洞以千数,无人敢入。有采樵者,误入洞,迷路不能出。见数黑人,浑身生毛,语兜离似鸟,以草结巢,栖于树巅。
《识小录》载,宜州产一物,如人,长丈余,遍体鳞甲。初据野寺,食畜兽,浸淫及人,峒丁多为所害。
这个宜州所“产”的怪物,外表像人,却长了一身鳞甲。是独出仅见的创生异兽。
(未完待续,接下篇)
请注意这是长篇连载,后文更精彩。有大量古今中外文献记载的神奇诡谲的生命创生事件。敬请关注。
(本文所用图片系作者自拍,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