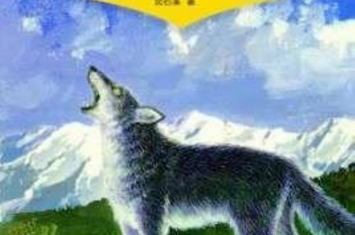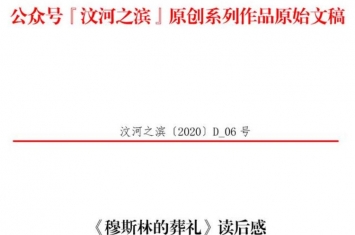三五个老头,总是围在一起,或坐或站,嘻嘻哈哈,拍拍搭搭,全无规矩,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随心所欲。唠什么呢?往大了说,日月星辰、战争和平、国家大政,百姓心事;往小了说,每个人几十年间的蹉跎岁月,几十年后的生老病死。
哥几个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真事似的;有时云淡风清,你对我对大家都对,没什么正经的事情。说到乐处,大嘴叉子各个扯到耳根子上了,身体都被自己的笑声震得一颤一颤的,像动了机关。但不同的话题,惹起的笑声不一样,有时是明朗地笑,有时是神秘地笑,有时是鬼祟地笑。时不时地还有人乜斜着眼睛,频率很高地偷窥着路过的老太太地笑。当然,这样子也适用于对“假想敌”的嘲笑,——这个“假想敌”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无中生有的编造出来的人到多数是有影射的人。反正只要可口、可乐,老头们就开怀大笑一场(据说每天大笑一场可以长寿数秒,多笑多得。不厌其笑,可以百笑百赚),其

表情动作虽不能说猥琐,至少嫌疑了旁人。
“老不死的,烦死了!”正常遛弯的老太太心里不悦,脚下生了风远远地绕了过去。那天有个公园管理者过来捎话,大意是,公共场所,小声点。
老头们并不收敛,反倒诘问:碍着谁了?捎话的主儿也不解释,向斜里努一努嘴便离开了。那斜里的方向正是越走越远的几个鲜艳的背影,虽然脚步散漫,但臂弯上的丝巾在空中招摇着,很是醒目。
老头们也知趣儿,懂事地围坐下来,开始下象棋。象棋是公园里安置的磁铁象棋:在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桌上,用玻璃罩着,铁链连着,丢不了,用起来很方便。这次来了六个老头,四把椅子不够分,身材壮实的老梁便让了贤,做旁观者。细高的长腿老肖借口坐着不舒服,也灯柱一样立在一边,把自家的嘴按了开关,滔滔不绝字字珠玑——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说个没完没了。大家相熟,也不在意。
老梁一声不吭,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棋桌,可脸上是愣愣的发木,心里头汤汤水水稀里哗啦的。老梁方头重耳,长鼻阔嘴,大眼微凸,很有三星堆青铜面具的风格(说不定还真就是那位面具原膜的传人)。更巧的是,他热衷于古物,痴迷于这个行当,过去没少研究、倒卖古董旧物,这些年下来,也赚了一大屋子瓶瓶罐罐,几大箱子珠珠儿串串儿。如今玩古董的行市降温了,他那些东西不值几个大钱,但他也没有卖的打算,那可是他命里的靠山、血里的氧气。
老梁现在说话办事是比较走心的,是这些人里的讲究人。
从前在企业老梁是妥妥的技术人才,车钳铆电焊,没有哪个工种他不能上手的。他有过很多第一,第一个入厂年龄最小的人——只有16岁,第一个在厂里开上机动车的人,第一个小车司机又同时驾龄只有二十二天的就被领导刷下来的人——车速原因,致使领导湿了裤裆,第一个用机床车出高精度仿进口零配件的人(当时给国家节省了很多外汇),第一个厂里的高级技工,第一个下岗又被找回来的人,等等。当然最要命的第一,是他的暴脾气在全厂三千多人里独一无二。不止暴,暴起来乱跳,跳起来高高,真往墙上撞自己的头呀,梆梆的,谁拉跟谁来。
一时间,没人能管得了他。
说来奇怪,一个蔫巴得像是一片落叶一样,又薄又纤细的女人一出现,他立马回归正常,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这个女人是他师傅的闺女,她后来的媳妇。有工友好奇,问他原因,他说她“有劲”,闻者诧异,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一碰就倒的小女子怎么就“有劲”了?她在风中可不止一次地凌乱了,连自行车都扶不稳。还有她女儿靓靓才两岁她就抱不动了,总是跟着她跑。要说她跑得快干活麻利倒是真的。“力量”这个五大三粗的词儿跟她可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这女人名叫宁亚丽,她娘家的女人都和她一样的身形,纤而薄,略带点憔悴的样子,但五官安置的精巧标致,极富风姿;娘家的男人都细而挺,略带点忧郁的表情,相貌上有一种来自五湖四海的感觉,五官总有些不搭。好在这宁家人脑子都好使,谋生不用干粗活。宁师傅老中专毕业,原本和他媳妇都在学校教书,后来才转到工厂搞技术。
所以,宁亚丽怎么就“有劲”呢?怎么就能以弱制暴呢?纠结像蛛网一样粘上工友们的额头。脑子快又善于琢磨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灯柱”老肖——那时候叫小肖,他是电工班的学徒,有事没事爱往老梁——梁留杰这边凑合,因为这里年轻人多,热闹。他把“有劲”这个词当作花生饼放在嘴里嚼着,嚼着嚼着,咂摸出味儿来了,心上一热一动,身体就敏感了,悠悠怨怨得差不点把裤子弄湿了。看看没人注意他,便用力地按了按自己,算作是对自己裆下物的安慰和警告。“灯柱”兴奋了,觉得满脑子都是灵光,一定要尽照射放出去。他一提醒,身边的人立刻感应到了,青年小伙子们都手忙脚乱地亮了。这会儿正近中午吃饭时间,赶巧做仓库保管员的宁亚丽和她的小姐妹一起走过来,灯柱他们的眼睛就一齐放起绿光,狼视着她们娇俏的似乎放着热气的身影,想入非非。
“吃饭去喽!”,梁留杰一声招呼竟然吓了他们一跳,纷纷转过姹紫嫣红的脸来,一个劲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对不起吗?他用眼神问大家。工友们这才如梦初醒,于是轰笑着出了车间大门,填肚子去了。梁留杰显然感到了暗流涌动,虽然没人跟他说。他沉住气,什么也没问,想暗暗观察。吃过饭,小师弟悄悄地蹭过来,神神秘秘地问他:“师哥,嫂子会功夫呀!内功叫做‘有劲’是吗?,师哥,能让嫂子也教教我内功吗?据说会功夫的人天下无敌……”梁留杰还没有听完,蹭一下跳起来,脸都红到头发稍了,他大喝一声:“闭嘴,小崽子!”又转向大家,“谁嚼舌头根子埋汰我了,带把的你就站出来!”可怜的小肖在众人的注视下,早没了光亮,倒像是一根不好脱皮的山药,浑身连坑带毛地杵在原地,进不是退不是,又窘又怂。若不是宁亚丽及时赶来,小肖的皮囊准变成梅花鹿了。
小肖还就是偏执,第二天找上梁留杰非问出“有劲”的正确答案不可。梁留杰粲然一笑,说:“有劲就是有劲,哪有那些歪门邪道。”说罢,叹了一口气。小肖知道梁留杰的脾气,但凡他叹了一口气,那一定会说下去,不然他是不会露怯的——谁见他叹过气呢?也就只有他“灯柱”有这个机会听到。他和留杰是同学,毕业之后都留城了。小肖上面三个姐姐都下乡了,到他这儿,就可以留城。留杰在家行二,一个姐姐下了乡,却死于意外。底下有四个弟弟,个子都没长起来,鼻涕却是一个比一个长。他们的妈妈身体特别不好,差点瘫痪。所以,家庭实在困难,老二就不用下乡了。留杰上学早,毕业那年没满十六周岁呢。
这之前,全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梁爸爸肩上,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他总说自己是给娘几个扛长工的,所以边干活儿边骂骂吵吵的,脾气很不好。其实梁妈妈每天都没闲着,她拖着个病身子从早干到晚,一刻也歇不着,只是干活太慢,做一顿简单的饭菜就跟别人做一顿大餐一样。缝缝补补的活计就没见她白天干过。晚上点灯熬油(那时总停电)地干,干也干不完,梁爸爸看不惯就忍不住发火,骂媳妇除了会生孩子什么都不会,不如死了好。梁妈妈一边小声啜泣一边小心地收拾活计,生怕老家伙尥蹶子打人。看她平时没精打采的,可是特别护孩子,家里外边不论谁决不能打她的孩子,假如她的孩子在哪受了欺负,她会不问青红皂白,上门找人家拼命要赔偿。她挂在口头上的话是“她妈妈命贱,儿子可是大命人。白打了人不行,要按价赔钱”。至于什么价,全在口头会气儿。时间长了,家家有提防,都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惹梁家人。不过,孩子们照旧在一起玩儿,打打闹闹是常有的事,但鼻涕孩儿们谁也不回家说,怕说了,就没有同龄孩子跟他们玩了。
梁爸爸几乎不管孩子们的事情,他只管干活。那年头家里活是真多,不像现在这么清闲。后来老二留杰能帮上忙了,却总是跟他干不到一起去。老子说二子偷奸耍滑不踏实,儿子说活该你挨累干的就是苯活。比如“买大件东西,你借个手推车,出去一趟什么粮呀煤的劈材呀,顺带脚都到家了,用不着一趟一趟地往外跑,费时间还费力气。”留杰说,“你修什么东西找什么人,也不用自己瞎整,越整越不好整,整来整去整坏了”。老子还没听完,立马咆哮了:“你懂个屁!借车不搭人情吗?找木工泥瓦匠不花钱吗?自己倒是偷懒省力了,家业败了!以后你踏踏实实出力干活,别整这些邪门歪道的”。留杰不服气,就跟他争辩,他老子气得乱蹦却拿他没办法,常常憋一肚子气没地方出。
放下手里活想赶紧吃饭吧,一问媳妇菜还没做完呢。不等菜了,干吃饭吧,结果一看,饭夹生了。老梁对着媳妇就是一顿骂,怎么伤自尊怎么说。媳妇更手忙脚乱了,慌慌张张的不是打了碗就是掉了碟子。若赶上留杰在家,就紧着上前给妈妈帮忙,一会儿做好了,再躲到一旁看着爸爸独自一个人把着大饭桌子狼吞虎咽。爸爸吃完了,再干一会活,然后就回屋睡觉去了,——他是中午觉也要睡的。这时候才轮到他和四个流鼻涕的弟弟吃饭,妈妈还要晚一些吃,因为她要给爸爸“挤脑袋”(按摩),这是爸爸规定的必不可少的规矩,每天如此。等到妈妈来吃饭时,饭菜早凉了,或者没剩下多少,可是直到爸爸睡醒,妈妈的饭还没有吃完。如果看到爸爸的脸色不好,妈妈就撂下饭碗去忙别的,有时偷偷吃上一口,这顿饭就和下一顿饭连上了。爸爸心情好的时候,就跟孩子们叨咕:“你妈妈是饿死鬼托生的,一天都在吃饭,咱家的粮食都让她造了。”
有一次饭做少了,其实也不是做少了,是因为那天全家人托了很多煤球,把肚子累空了。妈妈又煎了很多小咸鱼,所以吃到最后,饭没了。妈妈只好找些剩饭吃,结果上吐下泻,差点没起来。可是第二天中午,妈妈依然爬起来干活,中午给爸爸挤脑袋。因为身上没劲,手上力道就不够,这就惹火了爸爸,骂她“白吃白喝白活,养你有什么用!”之类的话,骂着骂着他睡了,妈妈却晕了过去。留杰那时正在在外屋吃饭,只听到爸爸的骂声停了,呼噜声响起,却不见妈妈出来吃饭。等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劲儿,赶紧进屋一看,妈妈晕倒在爸爸的头顶,像冬天饿死在枯木旁边的小麻雀一样,只有不合体的灰色衣服羽毛般堆积在她瘦小的身体上,而爸爸粗鲁的呼吸则风一样凌厉,毫无察觉。留杰本能地惊呼起来:“妈妈,妈妈,你怎么了?起来,妈妈!”鼻涕小兄弟们批了噼里啪啦地跑过来,跟着一起喊。
梁爸爸吓了一大跳,翻身跳下炕,他一眼看到媳妇苍白的脸,以为她没气了,“嗷”一嗓子惊天动地地咧开大嘴哭起来,还不忘打了自己一嘴巴子。留杰愤怒地回头瞪着他说:“我妈还有气,没死,你嚎什么!快去卫生所找陈大夫。梁爸爸嘎巴一下停止哭声,趿拉着鞋就往外蹽,心里紧张,腿脚也不好使了,一路上磕磕绊绊的,好几次险些摔倒。等陈大夫过来,梁妈妈已经睁开了眼睛,半倚在留杰的臂膀上喘气。梁老三应杰端着白瓷缸子喂妈妈喝水,老四老五站在炕沿边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着呢。陈大夫坐过来,给梁妈妈把把脉,对着留杰说:“没什么大问题,她就是身体太弱了!让她多吃点饭,不要太劳累。”看着留杰频频点头,又转向患者宽慰道,“别总惦记着干活儿,活儿是干不完的。要注意休息,到时候就吃,到时候就睡。记住了?”梁妈妈有气无力地回应着:“吃的挺好。睡的挺好”。一直在地上不停地搓着大手的梁爸爸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媳妇的脸,这时正要搭话,看见陈大夫向他使眼色,就跟着走出来,回头告诉留杰说自己去送送大夫,一会就回。留杰这边听了陈大夫的话,就赶紧嘱咐弟弟们看好妈妈,自己到外屋给妈妈热饭去了,还给妈妈加了一碗鸡蛋汤。
陈大夫见老梁跟上来,咳了两声,使左手推了推眼睛,右手照例按着医药包,也不看对方,竟自和风细雨地说话了:“老梁啊,嫂子身体太弱,禁不住折腾了。我告诉过你,晚上要有所节制,避开那几天,你看看现在她又怀孕了。”
怀孕!”老梁脱口而出,两个大眼球差不点掉出来。陈大夫并不吃惊,老梁平实就好一惊一乍的,何况又听到了意外消息。
“你四十几了?”
“你问这干啥?”老梁还没从刚才的复杂情绪里出来,听到陈大夫的问话就有些懵。“我不是大你五岁吗?”
“四十六岁了,她也过了四十岁。都不是当年的青春年少了,你悠着点,心疼点她。”陈大夫给他们掐算着岁数,再一次叮嘱道。老听出话中之意,一张大脸先就紫红了大半儿,搅着手嗫喏着:“也不是没注意,她那玩艺儿来的不准时,短了几天就回去了,长的没个头儿,那谁也不能总憋着。”他偷眼瞄了陈大夫一下,见他没反驳,继续说,“一个大老爷们……一大帮孩子……成天不得闲……累了,不是解乏?我不信你陈大夫娶个媳妇就为了看着?”
陈大夫咳了一声打断他,非常严肃地提出警告:”老梁,这事儿你得听我的话,决不能随心所欲。你媳妇的身体情况你清楚,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你。记得当初你们结婚时,我就提醒过你:她身体太弱,她妈妈和两个姐姐都是早夭,遗传上讲有缺陷。你要不好好爱惜她,恐怕用不了几年,你屋子里就没有暖和气了。我不是吓唬你,后果你自己想。你听我说,别急着插话,”陈大夫拦住老梁的要出口的话头,抬眼看看快到自家门口了,就站住,极其认真地按住老梁正要挥动起来的右手说“这样这样,也不是说从此你就当了和尚,但要有度,频繁了不好,那事儿不能当饭吃,要考虑到对方的接受能力。现在,她又怀了孕,你更该消停一些,一方面安胎,一方面给她个喘息时间。”
老梁早听明白了这些道理,可嘴上就是犟:“我还不让她喘气了?看你说的,他又不是租来的,是我明媒正娶的女人我知道心疼。从前……你别总提从前。从前我对她太那个着迷了……早就过了着迷的时候了。”他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陈大夫表态,“好,我听你的不总那个了。”
陈大夫拍了拍老梁的胳膊,又推了推自己的眼镜继续叮咛道:“给她做点可口的,她这几天需要补补身体。尽量别让她动体力。”老梁频频点头。
老梁回转身往家里走去,想着自己都四十六了?不可能吧,怎么总觉得还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呢,动不动就浑身冒火,火苗子腾腾地烧着,有使不完的力气,吃不饱的胃口……女人是最好的泄火对象。怎么她也上了四十了?他只记得自己比陈大夫大五岁,比她大五岁。若不是刚才陈大夫给算好了,自己还真答不出来今年多大岁数了。他想,“津津计较的小陈”,还是老样子,人是好人,就是津津计较、啰哩啰嗦。老梁很得意年轻时给陈大夫起的外号,那真是灵光一闪,竟然用上了成语,谁敢说咱老梁没有文化?他骄傲了好几年,不仅充分打击了说他没文化的那些人,还让陈大夫放了手,不然,她怎么就成了他老梁的媳妇。
当年,他追求得好辛苦。那时候大家都叫她“朵儿朵儿”的,就是花朵的朵,又嫩又鲜亮,虽不是大美人,但朵儿绝对是最水灵的女孩子,水灵得跟绿豆芽似的。说起来也可怕,她妈妈和姐姐们都是一样的相貌,水汪汪的眼睛滴溜溜圆,红嘟嘟的小嘴像花瓣儿,小腰细的风摆柳,皮肤白得像棉签儿——那时他正好去卫生所拿药,是班上有人感冒了,让他顺路给捎点药回来。巧的是一脚踏进卫生所的门,正看见朵儿跟小陈大夫要了几支棉签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呢。正午的阳光从明亮的玻璃窗子撒进来,铺在他们满是笑容的脸上,像张画一样好看。挺好看的画面,他却不知怎的心里突然觉得不舒服,觉得一向和顺的小大夫包包愣愣的。他取了药,却好像丢了什么东西,回身去找,又找不到。知道自己什么也没落下,只好讪讪地走回去。人回去了,心下总有失落感。
从此以后,女孩儿面条似的手指拢着的那几只棉签就总是怼着他的心,怼得他心里又疼又痒。那段时间,他找了各种借口去卫生所,却一直没有再见到她。“有事儿?”没事儿“。和小大夫的一问一答中,他对小大夫简直起了怨恨。有一次,他实在无法忍受心中的苦楚,在路上截住小大夫直接问道:“你把她藏哪了?”小陈正匆匆走着,冷不丁听到问话,一头雾水。
“我藏什么了?”
“棉签儿”
“可笑!,棉签有什么好藏的?”
“拿棉签的女孩儿!”
……
“就是那天我在你们那里见到的:个子不高,长得好看的……拿棉签的那个……”他脸红脖子粗地申诉着,恨自己没有太多的描述能力。
“你找我表妹?”小大夫终于弄明白了他奇怪的语言,“她叫朵儿,不叫棉签儿。她不在这里上班。你有什么事?”
“你表妹呀!我说的呢,那么随便!呵呵,长得是像。”他于是放松了脸上的肌肉,铺陈些笑容出来,他有求于人嘛,“她在哪里上班?”
“与你何干?”想不到小大夫并没有看中他,冷冷的撂下一句话就走了。
他窝囊了好多天,一筹莫展。在卫生所周围踅摸了好几次,人家小大夫绕道走,就是不理他。他是百爪挠心。
其实老梁年轻时,相貌一点不丑,发重眉浓,一双大眼像藏身岩下的猎豹,总有跃跃欲试的态势。直来直去的鼻梁,稍显生硬,但敦厚的嘴唇又让人看到男性的宽容与诚实。他中等个,体态灵活,就是脑筋不活好认死理儿。自从见到了朵儿,就一眼万年,雷打不动了。
后来,他妈妈爸爸托了人,去找小大夫家里人打听,说媒,才有了一些眉目。但小大夫始终不松口,说他太粗鲁,担心表妹受气。因为朵儿的妈妈和两个姐姐在这几年相继过世,家里只剩下她和父亲了。朵儿的二姨也就是小大夫的妈妈,心疼她,就常常叫她过来说说话吃顿好饭,极尽所能地给她母爱亲情。同时也担心她柔弱的身体,再不愿看到悲剧重演。小大夫祖上是十里八乡有点名气的郎中,所以一家人都是从医,对生命也就更看重。尤其是朵儿家庭的特殊情况,他们更是不敢有一丝含糊。这样,事情一拖就是一年过去了,梁家儿子再怎么努力也是求之不得。慢慢地父母灰了心,也屡屡劝儿子放下。可是他们的儿子偏是个宁种,为此把身体耗费了很多,你说这是不是命?他本来也不是胖人,这下子瘦的脱相了。
他是铸造车间的工人,干的是重体力活。每到中午,别人都去休息娱乐了,他就独自坐到树下,把树叶揪下来摆弄,有时放到嘴边吹气,慢慢的吹出了调子,摆弄出了形状。他就在这里想着朵儿,树叶在他嘴里颤动着悠悠地委婉起来,手里的枝条也变成了小筐小笼。事情很快传了出去,小大夫有一天中午走过来,一边看着小梁专心于自己的事情一边和他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临了拿起他刚编好的小鸟笼说:“光有誓言不行,一定要保持长久。我可以给你通融一下,但主要看朵儿的意思。”
也是凑巧,那天朵儿的爸爸过来跟姨姐姨姐夫说自己的婚事,原来早有人给他介绍个寡妇,虽说带了个儿子,但是人很好,是同一个工厂里的职工,还是厂里的劳动模范。姨姐当然说你相中就好,顺便把自己儿子小大夫的话简单扼要地说给他听。朵儿爸爸回去又说给女儿听。朵儿不知道对方是谁,听说和表哥一个厂子的,就去找表哥探听探听。小哥俩正在卫生所里说着话,小梁和几个人就走进来了。小梁的手上滴着血,啪嗒啪嗒地撒了一地。几个工友大呼小叫的,招呼大夫快点给处理包扎一下,唯独伤者一声不吭,平平静静。小大夫赶紧拿出医疗用具,清洗消毒,仔细查看一下伤口之后,去里间屋子拿麻药准备缝合。这空隙,大家才看到了站在圈外的朵儿,连忙殷勤地让座。时隔一年多,小梁又见到了心上人,心里的热血迅速涌到脸上,脖子上,额头上的血管像安上电泵一般鼓动着红色液体奔腾翻涌,上窜下跳。但是他的眼睛赶紧逃开了,不敢和朵儿对视。日思夜想的妙人儿啊,万一给她吓着了,他会背一辈子心债,还不清,无处还。他想,如果自己不能给她最光彩的一面,也不能让她看到最孬遭的一面。偏偏今天她来了,偏偏今天他受伤了。受伤了不说,满身油污灰尘,头发犹如黑毡头,鼻子像个铁疙瘩……形象糟透了。这时小大夫大声喊着:“王大夫,还有没过期的麻药吗?”另一个屋子里急忙走过来一个人,是不老不少的王大夫,他们都认得。王大夫也进去找了一会儿,可能是没找到,匆忙打电话联系大医院。小梁看明白了,不再沉浸在自己快乐的羞赧里,毅然要求不用麻药。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刮骨疗毒”的壮举。小大夫也敢下手,生生地给他缝了七八针,算是给他左手的虎口处合了龙。就这事,坏事变成了好事,朵儿在一旁偷偷观看,没见他皱一下眉毛,她佩服极了,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于是,当着他的面,她冲表哥要了摆在办公桌上的小鸟笼子,红着脸走了。
后来的新婚生活不用说,你恩我爱,和和美美。不料,接二连三的生孩子,让朵儿的身体吃不消了。她原本就弱,更兼家务活也重了,同时还要没完没了的应付老梁的床事。及至大女儿意外离世,她自觉得身上的零件彻底七零八落了,精气神趁机逃之夭夭,她大病一场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那时,留杰刚刚十二岁。
老梁刚开始特别心疼她,总是让她多休息,尽自己所能安慰她照顾她,可是从前水做的朵儿不见了,留下来的是一个做事慢慢腾腾、说话哼哼唧唧的半老婆子。到了晚上,老梁要和她行夫妻之事,她是能躲就躲,能拖就拖。做了,也不尽心尽情,只不停地催他快、快,气得男人开始骂人了,甚至好几次想打她,终究是下不去手。后来,不管她愿不愿意,老梁爬上去,只顾自己发泄痛快,但过后,看到她一摊泥一样,也是于心不忍,就又是好言好语地谢她。但是不久他就发现媳妇怕他了,好像他是个吃人的妖怪,连话也不愿跟他说。老梁不懂这一切是怎么变化的,难道女儿死了,日子就不过了吗?家里还有牛犊子一样健壮的儿子,有什么担心的呢?他一如既往地工作着,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需要,理所当然地过生活。两个人不再聊天,从前的温存都被老梁付诸于老白干,与白酒热烈着交流着。倒有一样,天规一般不可破,那就是“挤脑袋”。厂子离家近,每天中午,他都回来睡午觉,午觉前,媳妇要放下手中的活计,坐下来给他按摩。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媳妇惯的他。朵儿是从姨妈那里学到的按摩本事,她本来也是想吃这碗饭的,但是姨妈怕她身体弱再累着,恐干不长久。姨妈是纺织厂医院的大夫,就求了领导安排外甥女做保管员工作(朵儿也是特困留城)。不成想朵儿结婚后生了这么多孩子,大女儿又早亡,让她身心俱疲。老梁还不体谅她,更使她的心凉到了底。
妈妈后来“小月”了,一病不起,就差没有瘫痪。留杰就这样没有下乡。(一)

分手后她跟我说你答应的我都记得,你却忘了你的承诺是什么意思
你肯定是答应过她什么事情,或者给过她什么承诺,你一时记不起来,但是她这样说就是对你还有感觉,期待你做到你的承诺,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兄弟,如果还爱她就去追回来吧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会不会忘记他曾经对你的承诺呢?
我们都说两个相爱的人之间,最喜欢说的是情话,甚至是一些承诺,其实越是深爱一个人,越不会随意的对她承诺,因为他知道对一个人承诺之后就必须要做到,而不会随意的去承诺,如果承诺之后做不到,那些承诺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是不舍得,忘记对你的承诺的,无论你们是否在一起,无论彼此是否仍旧相爱,只要曾经住进了他的心里,他就会记得这些承诺,不会改变。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出粗心的忘掉了那些承诺,即使你们已经分开,因为他知道,彼此曾经心心相印过,虽然曾经发生过的点滴,都放在心底,却不会遗忘。
其实某天哪个同学聚会再遇见彼此,他的承诺,或许只是一个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他都会为你保留,这么做并不是说他忘不掉你,而是证明他曾经真的深爱过你,所以不愿意放掉这些习惯。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无论过去多久,见到你也会表露出来,毕竟曾经深爱过,又怎么可能当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都说两个人相爱的人是心心相印的,让你守住一个承诺一辈子,或是一个小小的习惯,那么都算是对上一段感情,最好的见证。
都说曾经深爱过的两个人,再次见面时,并不会表现得多么热情。两人见面时相视一笑,或许是对过去的感情的肯定,也或许是一种释然…。
或许你忙着和其他的同学热络打招呼,但对于此,你也只是站在角落里,静静地欣赏。
一个真心在乎过你的人,他一定会守得住自己的承诺,记得说过的某些话,或者一个小小的习惯,无论再久没有遇见,他依旧会记起来,在你面前,他依旧会记得那个承诺。
曾经女生对男生说:“我不喜欢看别人抽烟的样子。”男生回答说:“那么,以后我在你面前绝对不抽烟。”可惜后来阴差阳错,两人没有在一起。
时隔几年后的同学聚会,然后再次遇见,彼此淡淡的相视一笑,便各自去和其他的同学聊天,但眼睛还时不时的望向她在的那个角落。
或许你也是一直记得对男生的承诺,从此,不让自己哭,要幸福。所以她永远都是笑的,甚至从未发一条沮丧的朋友圈,有时候也会难过,但都一直藏在心里。
男生和女生都各自记得自己的承诺,一直都遵守着,从未改变过。
长久地遵守一个承诺,一直深情不变,也只有对深爱过的人才会如此。
记得他们分手时,连一句分手的话都没有,只是阴差阳错,或许一些误会,彼此没再主动,便错过了彼此。
记得分开的那些年,每每夜里。你曾想起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她担心被无数次去翻看,却依旧没有勇气留言问一句为什么?有时候,想要道歉说一句对不起,仿佛又觉得有些多余。
有一种爱,叫默默的记住你,曾经说过的话,我对你的承诺,一辈子永不改变,即使彼此没办法,守在彼此的身边,但爱情又何尝需要朝朝暮暮。
彼此守在身旁的,不一定是爱,而两个不在一起的人,却又没有水,可以说他们并不爱彼此。
彼此时常记挂着对方,记得曾经在一起的承诺,守着一辈子,无论是回忆也好。即使不再想起对方,至少证明彼此曾经都深深的爱过对方。
曾经深爱过的人,即使分手了,也不卑不亢,不争不吵,但无论过多久,再见对方时,依然会那个唯一的她,保留那个独一无二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