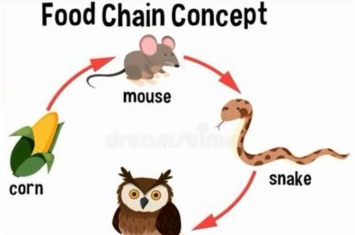提起司马迁,人们首先会想到有关他的两件事,一是他撰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一是他受过宫刑。可以这么说,由于司马迁的名气,在宫刑的人物史上,司马迁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也就与宫刑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生前把宫刑当作奇耻大辱。司马迁与宫刑的关系,也是历代史家和学者研究司马迁时避不开的一个话题。究竟宫刑给司马迁和《史记》带来怎样的影响,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较普遍的观点是,司马迁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是他个人生活的悲剧,却是《史记》增色的新起点。天汉三年(前98),正当司马迁埋头著述《史记》的工作进入高潮,“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被下狱受腐刑。司马迁身受腐刑,人处逆境,体味三重,对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从“以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而“发奋著书”,对国事世事从此冷漠不再关心。他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就是这种“较普遍观点”的推理逻辑,它的潜在话语是宫刑成就了司马迁,司马迁因宫刑而使《史记》的思想性与文学性更上一层楼。这种逻辑的极端发展是,明代的部分史家甚至认为要成功先自宫。
很明显这种逻辑是基于司马迁一定能战胜宫刑带来的奇耻大辱和痛苦使人深刻这两种前提的。其实面对宫刑所带来的奇耻大辱,在生与死的选择上,司马迁徘徊了多时。虽然他最终为了那无声的立言事业选择了生,但“刑余之人”的痛苦一直煎熬着他的后半生。所以我们不能仅从司马迁最终战胜困难的结果,从而把过程想得太轻松,高估宫刑的积极意义。
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所以司马迁视腐刑为奇耻大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司马迁出狱后,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此职本由宦官担任,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侍从左右,出纳奏章,位卑权重,被朝臣目为“尊崇任职”。司马迁不以为荣,反以为辱,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报任安书》中他满怀凄怆地诉说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菙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最”字,还要加一个“极”字,可以说把辱写到了极点,司马迁也痛苦到极点,“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经历如此痛苦,司马迁多次想自杀。“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平民奴婢面对羞辱尚且去死,何况我一个堂堂士大夫呢?司马迁一遍遍地拷问着自己。
但若是这样轻易死去,不能留功名与后世,“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况且又怎能对得其父亲的临终嘱托?这种痛不欲生的心境,这种矛盾交织的状态,严重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思考和写作进程,以至于到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史记》仍未最后定稿。父子两代人就《史记》写了几十年仍未完成,一方面说明他对史家职责的认真,但也不能不说明司马迁因宫刑在创作上受到了巨大干扰。由此看来,宫刑实际上对司马迁进行《史记》的创作起到了反面的作用,而不像那些论者仅从结果来看显得那么积极。
如果说宫刑之于司马迁真有帮助的话,那就是使他思想上更深刻,在对封建专制的批判上更强烈、更少顾忌,所以有人说《史记》是一部“谤书”。但是这种作用也不能夸大,不应把《史记》的思想性过多地归结于司马迁的受刑,这实际上是对司马迁的贬低。司马迁之所以有这么伟大的成就,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其父司马谈有意的培养,二十壮游开阔了视野,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临终遗言的鞭策,当上太史令之后能够“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的便利条件,强烈的史官与功名意识,深思好学、忍辱负重的个人素质等。过高地提升哪一个因素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