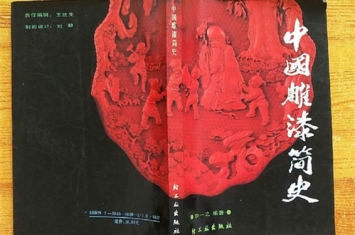手法主义是16世纪晚期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其主要特点是追求怪异和不寻常的效果,如以变形和不协调的方式表现空间,以夸张的细长比例表现人物等。建筑史中则用以指1530年至1600年间意大利某些建筑师的作品中体现前期巴洛克风格的倾向。
简介
手法主义是16世纪晚期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其主要特点是追求怪异和不寻常的效果,例如以变形和不协调的方式表现空间,以夸张的细长比例表现人物等。在建筑史中则用于指1530年至1600年间意大利某些建筑师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巴洛克风格的倾向。

维尼奥拉最早提出的设计口号内涵主要是指,建筑应该是“讲求技巧的艺术,是求新求奇的艺术”,其为巴洛克艺术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著名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维尼奥拉设计的罗马耶稣会教堂是由手法主义向巴洛克风格过渡的代表作,也有人称之为第一座巴洛克建筑。
手法主义时期
莱奥纳尔多·达芬奇的博大精深,米开朗基罗的宏大雄伟,拉斐尔的优雅妩媚,提香的自由奔放,凝聚了文艺复兴盛期的伟大特征,也为西方艺术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难以应对的挑战。依据历史教科书的说法,这些大师身后的时代即是文艺复兴晚期。
所谓晚期就是艺术开始衰微的时期,艺术家们浮浅地模仿前辈大师而没有自己的创见。这个时期大概延续了75年,直到巴洛克时期。这75年间的意大利艺术,史学家给了它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做手法主义时期。
历史
今天,艺术史家不再用这样的眼光看待这个时期的艺术了,他们普遍承认其创造性,认为手法主义艺术其实是对文艺复兴盛期艺术的古典平衡的一种反抗。这种风格首次出现在佛罗伦萨年轻的画家之中。
1521年,罗索·菲奥伦蒂诺创作了《将基督放下十字架》,充分表述了这种新的艺术主张。在深重的天空的衬托下,人物形式犹如蛛网式地伸展开来,这种斜条格构式的构图产生惊人的冲击力,在画史上前所未见。
画中人物激动不安但却坚硬不动,仿佛他们的躁动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冻雨凝固住了。刺目的色彩,明亮但却不真实的光线,加强了场景那噩梦般的效果。在这幅画中,艺术家旨在呈现一种主观的、甚至是幻想性的“内在视像”。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将古典艺术和自然和谐地结合了起来,那么,手法主义时期的艺术就是要使这种内在的视像凌驾于自然和古人双重权威之上,创造一种令人不安的执拗而富于幻想的风格,以表现人类灵魂深处的焦虑。
这种精神焦虑根植于画家自身。罗索的画友蓬托尔莫(Jacopo da Pontormo),性格古怪、害羞,最终将自己关在家里,与外界隔绝几个星期,甚至连朋友都不见。
他敏感的素描《少女习作》充分地反映了他自己的性格,被画者忧心忡忡地注视着眼前的空无,仿佛朦胧地回忆起某种精神创伤,希望完全从外部世界退缩到某个安全之所。
罗索和蓬托尔莫的风格在本质上是反古典的,代表了手法主义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很快为他的另一个侧面所取代。在这个阶段,艺术家不再描绘心灵的骚乱,更注重画面本身的形式变化。
它并不公然地对抗古典传统,也较少讲究主观情感,但在本质上仍然偏离了文艺复兴盛期那种自信而稳健的风格。帕米尔贾尼诺(Parmigianio)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in a Convex Mirror)代表了这种倾向。
从画中可见,这位艺术家的外表和蔼可亲,打扮讲究,画面笼罩着精妙的莱奥纳尔多式朦胧感。人物的变形,并非是随意的,而是有意的。其实,这变形乃是整幅画的主题。这幅画记录了画家在凸透镜中反射出来的形象。
前辈画家曾利用镜子帮助他们观察,如凡·艾克(Javn van Eyck)曾通过镜子检验形象,以消除变形,同时他还利用镜像直接反映画中的同一场面,以增加画面的见证真实性。
帕米尔贾尼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画透过镜子所见的自画像呢?他意在用镜子取代绘画,他的画其实是画在他特意准备的凸透板上的,以使它看起来就像一面凸透镜。他也许想以此证明,世上并不存在唯一准确的现实,变形其实就跟事务的正常形态一样自然天成。
然而,他这种科学的超然态度很快走向了另一极端。帕尔米贾尼诺和拉斐尔、乔尔乔内(Giorgione)一样,是短命的画家。
瓦萨里在《名人传》中曾记录,在帕尔米贾尼诺生命结束之前,他对炼金术着迷,整天沉醉于其中,竟忘了清理自己,“胡子满面,长发过肩,心不在焉,简直成了一个野人。”与衣装讲究的自画像中的画家判若二人。
帕尔米贾尼诺曾在罗马住过数年,从罗马回到故乡帕尔马不久,创作了他的名画《长脖子圣母》(Madonna with the Long Neck)。在罗马,他必定认真研究过拉斐尔的作品,在《长脖子圣母》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拉斐尔般的优美韵味,但他将拉斐尔式生母转化为新的类型。
犹如象牙一般光滑的拉长了的四肢,有气无力,象征着一种美的理想,它与自然的距离,如同拜占庭人物与自然一样遥远。人物场景也是随意构筑的,一排巨大的圆柱,毫无目的地占据画面的中景,前面站着一位与圆柱不成比例的先知人物。
整幅画作丝毫没有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自然和理性等古典价值,而画家似乎故意要打乱我们的期待,阻止我们用日常经验的标准去衡量画中的一切。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手法主义的含义了,它主要指一种“人为”的风格。“人为的”是一个中性词,而它的贬义就是“矫揉造作”了。然而,《长脖子圣母》是用明显的“人为”风格表现了一种超凡入圣的完美视像,他那冰冷的妩媚,其感人的力量,不亚于罗索的暴力。
手法主义艺术的精美,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中世纪艺术的图案化传统,布龙齐诺(Bronzino)的《托莱多的埃莉诺和他儿子乔凡尼·德·梅迪奇》(Eleanora of Toledo and Giovanni de'Medici)就是典型的例子。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画中人优美而繁复的服饰图案,而这华贵的衣饰上面的被画者头像,没有表情,宛如一尊优美光滑的瓷像,没有个性和母爱的亲切感,仅仅作为优越的等级社会成员的象征。
因此,手法主义艺术特别吻合某些王公贵族的趣味,托斯卡尼的大公极为赞赏这种风格,法王弗朗西斯一世也是如此。手法主义很快蔚然成为一种国际风格,一如哥特式艺术。
手法主义风格始于佛罗伦萨,鼎盛于威尼斯。廷托雷托(Tintoretto)是威尼斯手法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
廷托雷托曾在提香画室学画,在那里,他学会了老师的绘画技巧,然而,他是一位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前面说过,佛罗伦萨手法主义有两种趋向,一是反古典的倾向,二是优美雅致的倾向。廷托雷托要把这两种倾向合二为一。
同时,依据传说,他立志“要像提香一样绘画,像米开朗基罗一样设计。”他的意思是要把提香的色彩与米开朗基罗的素描结合起来,创造别开生面的新艺术。其实,廷托雷托与提香和米开朗基罗艺术的渊源关系,就如帕尔米贾尼诺和拉斐尔的关系一样奇特。
廷托雷托偏爱透视强烈、甚至唐突的构图,他笔下的人物姿态各级,动势激烈,往往有强烈的短缩效果。他在反宗教改革的环境中长大,他超凡脱世、充满炽热的虔诚心,但处事千变万化。他的性格与老师提香截然相反。
廷托雷托的宗教绘画富于情感启示力,站在他的巨作《基督受难》前,我们的灵魂即刻会受到震撼,宛如听见一声惊天霹雷,我们也会与画中人物一样不知所措,踉跄奔走。这幅作品是全景式绘画,从一个墙面伸展到另一个墙面,一直覆盖了护壁板,延展到天顶。
前景中的人物比真人的尺寸还要大,其他不计其数的人物动作幅度很大,透视短缩感很强,但这表面混杂不堪的人群,在幻想般的光线的照耀下,形成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统一整体基督孤立地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画面强烈的对角线,无不在基督身上交叉,在画面中心形成了双重三角形,牢牢地牵引住了整个动荡的画面,并突出了主要的形象与情节。
廷托雷托繁复动荡的画面,总是给我们极大的心灵震慑力,以致使我们来不及欣赏他所画的奇妙的人物细节。《最后的晚餐》是他晚期的重要作品,也最为壮观。我们知道,一个世纪以前,莱奥纳尔多·达芬奇以同一题材创作了一件旷世杰作。
廷托雷托的画,彻底否定了莱奥纳尔多的作品所体现的古典价值。基督的形象,虽然依然处于画面中心,但餐桌不再是横穿画面,而是斜放着,在画面形成了极强的透视感,以致坐在中心的基督的形象大幅缩小,我们只能依据他头上的明亮光轮确认这个形象。
画家分明是在画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而不是一个宗教题材。画面不但有十二使徒,还充斥着其他人,四处是盛装食物和酒的器皿,还有家养的小动物,场面嘈杂凌乱,充满日常生活的气氛。
然而,画家并非是为了画日常场景而画这些东西,他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气氛创造一种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的戏剧化对比。
画面有世俗的参加者,也有来自天国的出席者,那燃烧的油灯释放的烟雾神奇地变幻成天使乘坐的云彩,向着基督飞翔,而基督正把面饼与酒(代表他的身体与血)分发给使徒们。叛徒犹大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小得难以令人注意。
廷托雷托在这幅画中的主要意图并不在于表现使徒们听到主告诉他们有人要卖他后所激起的骚动,而是要用视觉形象再现圣餐变体的奇迹:世俗的面饼和酒怎样在弥撒中经祝圣后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
在廷托雷托之后,威尼斯最重要的画家是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这两位画家的风格截然不同。但两者都是公众心目中的明星。委罗内塞的代表作品是《[2]在利未家中的耶稣》(Christ in the House of Levi),表现的题材与廷托雷托的《最后的晚餐》相同,但表现手法和画面意境完全不同。
首先,廷托雷托将画面中的人物卷入了一种躁动混乱的场面,使我们一时看不清画面的细节。它像贝多芬的交响曲,把我们的情绪一下子带入高潮,而委罗内塞恢复了画面的平静,意在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参与画中活动,认清周围的人的一举一动。
在他的画中,没有任何超越自然的东西的迹象。乍一看,这幅画好像是文艺复兴盛期的作品,落后时代半个世纪。仔细观察,这幅画缺少文艺复兴盛期艺术所强调的关于人的理想观念。委罗内塞画了一场华筵,一场可饱眼福的盛宴,丝毫无意表现“人是灵魂的意图”。我们弄不清他原意描绘的是哪个基督生平事迹。
这幅画引起了教会的反感,有人状告他在画中加入“小丑和其他粗俗而愚蠢的东西”,有亵渎神圣事物之嫌。在他被召到法庭上受审时,他才给这幅画取了现在的名字。韦罗内塞否认对他的指控,坚持说自己有权描绘直接源于生活的细节,不论这些细节有多么“不恰当”,他都有权这样做。
韦罗内塞并不看重绘画的题材,因为,他相信整个可见世界是画家的表现范围,在这个范围中,他只承认一个权威,那就是他的感官,他的眼睛,而其他一切权威都应拒之门外。
这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当然会受到韦罗内塞时代的激烈反对,一直要到19世纪,人们才接受了它,印象主义画家们也迫不及待地打出科雷乔式口号,要到户外去画他们的眼睛之所见。在这一方面,科雷乔可以说是西方现实主义艺术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