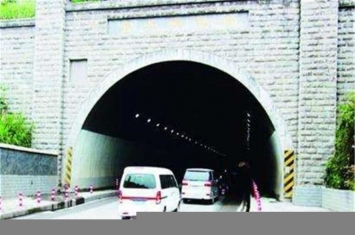路难行 人无怨
我从昭阳区出发,一路盘旋于大山之间,山道蜿蜒通向大山深处,威信县越来越近了。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川南、黔西北、滇东北一带集结。为何选择深入山高林密、道路险峻的云贵高原?毛泽东用“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诗句指出了原因。
“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是乌蒙山的简称,位于云贵高原西北部和滇东高原北部,山系呈东北—西南走向,是我国西南部云贵高原的主要山脉之一。乌蒙山最高的山峰位于云南省境内的会泽县南部,叫石岩尖,海拔3806米,空气稀薄。乌蒙山的主峰位于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境内,叫韭菜坪,海拔2900米。“走泥丸”是指险峻的乌蒙山在红军战士的脚下,就像是一个小泥球一样。当年红军有两支队伍经过乌蒙山区,一支是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支是贺龙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2月至3月,红二、红六军团在这座渺无人烟、道路泥泞的大山之中与敌军的10个师周旋了1个多月。乌蒙大山,天寒地冻,高原缺氧,粮食奇缺,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红二、红六军团陷入了自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最艰险的境地。紧要关头,军委纵队从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出发,在高山峡谷间沿着陡峭蜿蜒的山路艰难行进,翻越一座座高山,一路跋山涉水,终于抵达扎西镇石坎子村,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之所以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其完成了党和红军在指导思想上、领导体制上以及军事行动上的三大转折。
终于,红军走出了这片泥泞之地;终于,在86年后的今天,威信县扎西镇实现了“天路”通达、朝发午至,红军当年的艰难行走之路已成为历史的记忆。
望着拔地而起、一座连着一座的群峰,有的高耸入云,有的逶迤伸展,有的如飞腾的龙,有的像偃卧的牛,千姿百态,令人遐想无限。感受昭通,才能体会民众由贫穷迈向富有的欣欣之情。慨然陡生:山不在险,开拓则通;路不在荆,敢闯则勇;人不在权,为民则颂;文不在大,有义则圣。
不言苦 心却酸
千百年来,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稀薄的空气,山与路的险峻,一直困扰着昭通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出行。摆不脱“行路难、交通难”的日子,就难以驱散贫困的阴影。
何谓路?字典上的解释为:来往通行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居住,就会有路。早期的路,大多是众人用双脚一步步踩实或用石制器具一提一放夯出来的。
昭通的路,皆在高山峡谷间。山路浸染了无数开路者的血汗,每段山路的建成,付出了无数人的心血。谈及今天的路,人们的欢喜与兴奋泛在脸上;谈及往昔的艰辛,有的只是云淡风轻的回忆。
蜿蜒曲折的山间公路,从昭阳区通向各地的每座大山、每个山洼、每个乡村、每个昭通人的心底,如一条条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把修路致富的理念灌输给千家万户。我来到了镇雄县,眼前的一幕令人惊讶。
面对处处险峰的大山,纵横交错的山道,作家尹马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尹马的家在镇雄县瓜果村,他在镇雄县政府工作的时候,早上7时坐汽车出发,到县城大概是58公里,汽车要行驶12个小时。一天,他看见隔壁村的一位老人,手里拎着两个土豆,从他身边走过。有人问老人去哪里,老人回答,县城。尹马知道老人舍不得花钱坐车,肯定会走路去县城。他知道老人手里提着的土豆,就是老人一天的干粮。
尹马乘坐汽车要花一天时间,老人走路就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当时的公路是县级公路,一路坑坑洼洼,颠簸不断。当他到县政府下车的那一瞬,无意中看见老人正坐在县政府大楼的台阶上吃土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人怎么可能比汽车还快?于是,他上前询问。老人把最后一口土豆咽下去又喝了口水,才抬头对他说,走小路嘛,汽车绕来绕去,慢!
老人慢条斯理地说着,尹马仍然感到惊异:58公里,汽车行驶了12个小时,老人步行却先到!可想而知,当时公路的状况有多差。
若不是亲身经历,谁能相信这是真的!旁边的一位女士说,有些事儿现在说起来既好笑又尴尬,还有点心酸。这位女士从小跟着奶奶长大,每天早上都盼着太阳出来,因为镇雄县10天有9天是阴天。一旦出太阳,她就会高兴地坐在凳子上眺望远景,远处除了大山还是大山。她奶奶一辈子都没走出大山去看看县城以及县城外的世界。路在哪儿?山很陡峭,路就像在天上,她奶奶走不出去。
说到这儿,女士突然笑了。她接着说了一件好玩的事儿。一天,她同事和男朋友骑着摩托车去县城。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特别是下过雨后,有装着重货的大货车经过,压出许多大坑。同事的男朋友边骑摩托车边跟身后的女朋友说话。不知道摩托车行驶了多远,他突然觉得自己说了半天没有人回应。扭头一看,女朋友不见了!他惊出一身冷汗,急忙往回行驶,一路大喊着女朋友的名字。10多分钟后,他看见女朋友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哭……
这故事有笑,有泪,有心酸。让我感觉到,如果作家一味地坐在书房里,怎能听到这些真实却让久住城里的人想都想不到、编也编不出来的故事呢?
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批评作家采风:走马观花,吃喝玩乐。创作就是创作,采什么风,踏什么花呀!文章是能采得出来,踏得出来的吗?
我想,如果这位“有识之士”听了这些故事,他会不会也有所悟呢?凡事皆有两重性,不能以偏概全。作家一味坐在家中览尽网上的“美景”,如隔靴搔痒,虽偶尔知天下奇闻异事,但多是以讹传讹。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带着烟火气息的生活场景,百姓的甘苦,山风海气的拂面,是坐在家中永远无法得到的。当下一些人,以一台电脑、一瓶烈酒、一壶茶为乐,或者三五男女聚在宾馆里吞云吐雾,编造出一些经不住推敲的故事。对社会真容、生活本真一无所知的他们,所创作出的东西永远不会是贴近人民、贴近生活的鲜活之作。
面向大山,我心生敬畏,它曾保护红军,养育了这里的人民;同时也心生怨气,它给这里的人民以艰难、贫穷、闭塞。这或许就是生活的两面性吧。
交通兴 昭通兴
云贵高原,以空气稀薄、山高路险闻名。我们一路采风,深有体会。
在采访昭通市交通运输局的艾永练时,他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威信县城扎西镇到昭通需要3天时间。第一天到邻县镇雄县,第二天到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或黑石头乡,第三天才能到昭通。人们出行是件艰难的事,不到万不得已,大多数人不会出远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滇东北各县之间有了弹石公路;2000年以后,水泥路渐渐多起来,后来路面扩宽,在上面铺上柏油,有了柏油路;21世纪的中国,许多乡(镇)已修通了柏油路,来往已不再是一件困难之事。但是,当时威信县既无高速公路,更无铁路,山高路险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019年12月26日,对威信县45万百姓而言,无疑是个划时代的开端。那天,成贵高铁正式通车。以前,从威信县到四川省宜宾市,长途班车得颠簸五六个小时,而今坐高铁到四川宜宾站只需40分钟。这惊人的变化如梦如幻,原来到成都得六七个小时,现在只需3个小时;原来去昆明基本是“两头黑”,现在坐高铁只需4个小时……成贵高铁提升了威信县的交通格局。之前,威信县只有二级公路,连火车都不通,现在一步跨入了高铁时代。在外与人谈起这一变化,许多人总是满脸愕然,更多的却是艳羡!
如今,威信县除宜毕高速公路通车外,在建的还有隆黄铁路。隆黄铁路北起四川隆昌,南到贵州黄桶,全长497.4公里,是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规划建设的铁路。2021年4月,隆黄铁路隆昌至叙永段扩能改造工程初步设计获得四川省发改委正式批复。2021年4月23日,隆叙段扩能改造段首桩先期启动建设。短短几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密布威信县境内,什么叫巨变?这就叫巨变。铁路及多条高速公路的贯通,不但让人们出行便捷,还极大缩短了威信县与周边的距离。外出旅游、探亲访友成为县城人们新的生活方式。
“建设过程一定非常艰难吧?”我问道。“是的。”艾永练接着说,2021年10月16日,昭泸高速公路经过上千名施工者3年时间奋力建设,全线最长隧道清河隧道顺利贯通了。清河隧道地处昭通市镇雄县,全长6185米,为全线最长隧道,也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由于隧道穿越乌蒙山区多条断层破碎带,地质条件复杂,围岩自稳性差,施工中遇到大小塌方近百次。施工技术人员经过多次研究探索,发明了多臂钻凿岩台车,不但提高了机械化操作水平,也消除了安全隐患。
涌水问题是昭泸高速公路的施工难题,也是影响施工进度的主要因素。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建设者的大部分施工作业,都要头顶着不断从山体里涌出的水流,站在几十厘米深的水里进行。夏天,建设者们站在水里,有的人快虚脱了,休息一下接着干;到了冬季,他们站在水里,浑身被冻得发抖。没有人退缩,没有人因此而放弃。
据统计,隧道单日最大涌水量超过8万立方米,超出设计量的13倍之多。在隧道建设期间,累计抽排水量高达4200万立方米,两年半的涌水量相当于3个杭州西湖的容量。没有亲身体验,永远不会体味到在水里作业的累与苦、冷热与危险。
施工时,建设者采取了超前地质探孔,径向注浆堵水,在掌子面开挖时设置集水坑。仰拱开挖时设置积水井,把车行洞改造成积水仓,整条隧道共设五级梯级反坡排水系统,24小时36人管理。通过这些措施,由原来的月掘进30米提高到80米。
清河隧道的典型特点对于全国隧道建设都是一个“卡脖子”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施工队请来了同济大学研究团队,把清河隧道纳入昭泸高速公路复杂隧道群重点进行研究。经过研究,建设者们首先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建立了一个全空间地质数字模型,在施工过程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地质的变化以及隧道变形的情况,以保证隧道的安全掘进。接着,建设者们研发了新型的支护结构,在隧道开挖的过程中,可以实时保证隧道的安全。同时,在隧道壁内埋设了光纤传感器,实时把握隧道的安全信息,为后期隧道运营期的安全提供有效的支撑。
在隧道开挖过程中,还采用了地质雷达、超前水平钻探等先进科学探测手段,及时对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并结合具体围岩情况进行动态设计优化调整,应对坍塌、涌水等险情,确保隧道按期贯通。
“办法总比困难多。”艾永练脸上有了笑容。他接着说,昭通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高山与峡谷并存的特点,高边坡、堆积体大、岩溶地貌复杂,全年冰雪雨雾天气长达9个月左右,煤层区域瓦斯浓度最高时达到90%,桥隧比高达76%,施工难度可想而知。但在团队的通力合作下,这些困难都被克服了。
山默无语,绝非无声。站在群峰之下,发现昭通的山与东北的山不同,与湖北的峰有异,重重叠叠,挺拔天地,有启迪万物之能,有雄伟奇特之貌。万里长征路浩荡漫山,开山筑路大道连云贵,好一幅危峰立、怪石嶙、天梯险、路萦纡、势磅礴的天路神图。
天路通 美景现
在金风送爽的日子,我来到地处云贵山麓、金沙江畔的昭通。举目远眺,天高云矮,峰峦如浪,迎面吹来阵阵清风,传送着昭通人的希望和梦想。
昔日的昭通为交通要道,有着丰富的马帮文化、茶叶文化和朱提文明。世界日新月异,20世纪80年代,昭通的交通却阻碍了发展。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昭通人浴火重生,新的交通枢纽逐渐形成,昭通正在崛起。
在著名作家抒写“大道昭通”的开幕仪式上得知,5年来,昭通有效破解资金、技术、人才、管理“四大难题”,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累计完成综合交通投资1658亿元,占全省的14.4%;新建高速公路12条,通车里程从136公里增至近800公里,跃居全省前列;打通出滇、入川、进黔高速通道11条,除永善县外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硬化农村公路近2万公里,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05万公里;成贵高铁建成通车、渝昆高铁开工建设,昭通机场直飞航线从1条增至11条,天堑变通途的梦想逐渐成为现实,为如期攻克绝对贫困堡垒、顺利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加快昭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进程提供了强力支撑。
昭通人天堑变通途的梦想,是在高海拔、高寒缺氧、积雪冻土、山势险峻的建筑工程难题上实现的,形成了集公路、水路、航空为一体的立体交通体系,展现出昭通交通枢纽的恢宏。昭通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逢山凿隧、遇水搭桥,历经艰难险阻,终于使昭通不再不通、不再有阻。
我来到“滇川门户”石门关,眼前的景象让我不敢相信:秦驿道、水道、铁路、国道、高速公路,居然“五道”交错有致,蔚为壮观。如此神奇的“五道”呈现在我眼前时,一时语塞,没有更好的词汇来赞美,只想起一个很俗但很能表达心境的词:叹为观止!
5天的昭通行,我为所见而震撼:高铁呼啸般地如奔马,银鹰从山头、从大桥、从村庄轰鸣划过似闪电;为所闻而欣慰:路通了,产品好卖了,有钱了,富裕了。我父母家在镇雄县,过去回家是一种受罪,现在回家坐高铁是一种享受,交通为我尽孝铺就了一条坦途。
大道不兴,蜗居在群山之间的人们只能望山兴叹;交通不畅,山珍野味永远“飞”不到天南地北;“交通先行”战略打通了民生之路、富强之路、产业之路,小到出滇、入川、进黔,大到北上广深,飞而即到。在车上,不知是谁忽然诗性大发,吟诗一首:“天路通南北,时间催车快。世界不遥远,脉动笑开怀。”
行走昭通,感受昭通,我看到了建设者们在莽莽乌蒙山中开山辟路、挥汗流血的豪气。“愚公移山”大无畏的精神和他们“大禹治水”的中国智慧造就了昭通的公路史,同时也造就了一部新时代的公路史!
如今,封闭的观念、闭塞的道路,被眼前一条条穿越崇山峻岭、四通八达的大道“通关”。很难想象昔日是如何“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因为历史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已然翻篇。希望,正在昭通大地上冉冉升起;梦想,正在乌蒙山川上放飞。在即将离开昭通的时候,思绪与感慨交织一起,心潮澎湃之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连峰际天鸟不飞,乌蒙盆地江河围。
深山绝壁开天路,历尽艰险人不悔。
铁牛飞奔峰峦悦,银鹰展翅大地美。
金沙江水拍手贺,高桥一架道如碑。


作者简介
赵晏彪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外作家交流营组委会主席,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剧本部主任,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民 族文学》原副主编。“中外作家交流营”“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剧本遴选活 动”“中国文学对话诺贝尔文学论坛” “金鸡百花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少数民族 题材电影剧本征集活动”“中国土家族 文学奖”等活动及奖项的发起人之一。参与《半条被子》《漂着金子的河》等多部电影制作策划。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媒体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出版著作12部。作品多有获奖,并译成英语、韩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出版。
来源丨@昭通日报 微信(ID:ztrbwx)丨播音/彭晓雨
编辑丨雷明娟
编审丨莫娟
值班领导丨秦勇
校对丨彭晓雨
投稿邮箱丨302626508@qq.com
广告咨询丨0870—3191969
@昭通日报 微信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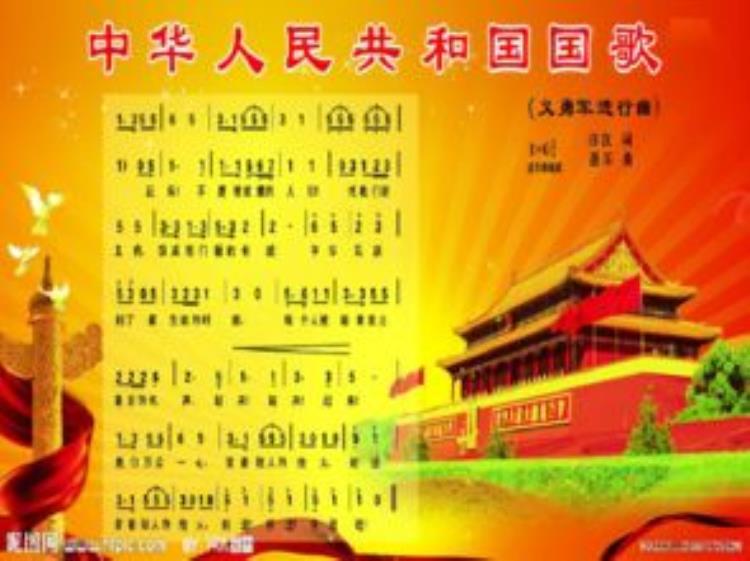
天路作词契合时代精神风貌,放歌祖国前进心声反映了人们怎样的思想感情?
映了戍边将士杀敌立功、保卫国家矢志不渝的决心。表达了国家有事,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古从军行七首(其四)是唐代边塞大诗人王昌龄的名作古从军行七首中的一首,其中“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堪称是名篇中的名句,表明边塞将士誓死杀敌的气概。
全诗如下: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译文如下:
青海湖上乌云密布,遮得连绵雪山一片黯淡。边塞古城,玉门雄关,远隔千里,遥遥相望。
守边将士身经百战,铠甲磨穿,壮志不灭,不打败进犯之敌,

走近天路守护者
这是一条镶嵌在雪域高原上的天路——铁轨沿着青藏高原的脊背笔直而上,越过草场、跨过河流、穿过高山,抵达茫茫雪岭背后的美丽远方。
抵达是人类的天性。过去久远的时间里,为了抵达,我们在横亘的高山前学会攀登,在难测的深渊边懂得涉渡。
然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天路旁选择了停驻。
汽笛长响,列车飞驰而过。那些站立的身影,几十年如一日。自1984年一期工程通车以来,在近两千公里的青藏铁路沿线,一代代武警官兵默默守护着这条高原“生命线”。
关角,天路必经之地——它在藏语中的意思为“登天的梯”。一进入关角山,就进入到氧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有“世界高海拔第一长隧”之称的关角隧道,是人类在此留下的伟大印记。
沿着青藏铁路,我们走近守护关角隧道的武警官兵,走近天路守护者,在抵达的脚步中感受坚守的意义。
走近驻守世界高海拔最长隧道的武警官兵——
青春守望 幸福飞驰
青藏铁路沿线,武警青海总队某中队官兵担任关角隧道执勤任务。 王金兴摄
车窗将列车内的景象显映出来,窗外的漆黑不断刷新,壁灯有规律地一闪而过,列车与墙壁之间激起持续而低沉的回声。
车厢里,旅客们的交谈声笼罩在黑暗的混响中。
十几分钟过去,这辆“昆仑号”城际列车依旧在幽暗的山体中穿行。
“居然还没有过完,这个隧道可真长!”一名年轻人满脸兴奋地和同伴说着。看样子,他们是第一次到青藏线旅行的游客。
“这是关角隧道,有32.69公里,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第一长的隧道。”一旁的蒋红伟忍不住接了话。
作为一名在关角山驻守了12年的武警老兵,休假返程的上士蒋红伟讲起关角山的风土人情。
这种情景,在蒋红伟的军旅生涯中并不少见。他所在的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某中队,就守护着眼前的关角隧道。那句他脱口而出的隧道介绍语,用红漆大字,写在从营区通向哨位的路上。
跨越20多分钟的黑暗,列车瞬间跃进大片光亮里。飞速之下,铁道旁,哨楼和武警士兵的身影一闪而过。
看到不远处群山环绕的白色营房,蒋红伟心里默念:“关角,我回来了。”
夜间列车驶过的光带,就像城市霓虹的彩灯
休假回中队的第一天晚上,蒋红伟迟迟没能入睡。海拔升至3000米以上,骤然减少的氧气唤起身体对关角山的记忆。
他躺在床上,静静等待着。
23点30分,一声列车鸣笛划过沉睡的山谷。蒋红伟知道,这是一趟客车,在 旅游 旺季,大约有11到12节车厢。等床板停止细微颤动,一切又安静下来。
关角中队每一名官兵心中,都有一张熟悉的列车时刻表。
23点30分、凌晨1点、凌晨4点……每次因氧气稀薄难以入睡之时,他们都会在黑暗中等候并印证那一声声汽笛的响起。
高原广阔的草场上,河水舒缓流淌,成群的牛羊在闲云下低头漫步。这样的悠然景象,并非每一名驻守关角隧道的官兵都能看到。
全长32.69公里的隧道,将守护它的官兵分为一东一西两个中队。靠近西宁方向的官兵,一年四季静候草场由黄变绿,又由绿变黄;而靠近拉萨方向的官兵,只能看到四周的荒山岩壁。
蒋红伟的哨位属于后者。“其实也没什么区别!一场雪过后,哪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他说。
官兵们的身影,为关角山规律而枯燥的景色,增添了复杂多彩的 情感 底色。
士兵王聪挺直腰板,警惕地站在哨楼上,目送一列运煤货车驶进隧道。随后,他拿起对讲机,向值班室报告列车通过情况。
守在铁路旁9年,26岁的王聪只要听到汽笛声音,就能分辨出不同类型的列车。最初,站哨时间显得特别漫长,他会不自觉地数起车厢数量。看着列车渐渐远去,王聪内心也有所触动。
“最初看到火车穿过,会特别想家。尤其是过年的时候,车厢每一面窗子上都贴着福字。”王聪是家中独子,17岁就进了军营。小时候,他看完电影《遥远》,知道了圣女峰哨卡,一心想来雪域高原当兵。
来到关角山后,他才真正领略到心中神圣之地的另一面。红肿胀大、布满裂口,指甲因长期缺乏营养而破碎凹陷——王聪在哨位上站得笔直,胸前持枪的双手上满是高原留给他们的印记。
有些时候,从哨位看到车内的情景,会令官兵们心头一热。
下士何增成说,有次列车通过哨楼,即将进入隧道时,一个小男孩站在过道中面向车窗,对着他敬了军礼。那时,列车刚缓缓启动,他甚至能清楚地看到小男孩的表情。
那一刻,站在哨位上的何增成,内心充满自豪。
高原是荒凉的,但青春并不荒凉。在寂寞的守隧生活中,王聪喜欢上了摄影和唱歌。
“夜间列车驶过的光带,就像城市霓虹的彩灯。”远离繁华,王聪用自己的视角观察着关角山,理解着关角山。他的相机里,有高原繁密的星空,有连绵的雪山,记录着营区小树的顽强成长,保留着官兵笑与泪的珍贵回忆。
多少轻松或郑重的时刻,他也和战友们一遍遍地唱起那首《关角山哨所小唱》。那是他镜头里的画面,那是他们的青春岁月——
“巍巍关角山,漫漫隧道长,小小哨所寒来暑往。抬头仰望那雄鹰在翱翔,脚下是一条天路在远方……”
日复一日,他们走过这条路,也护卫着这条路
我们从一个中队出发,开车去往隧道那头的另一个中队。在盘曲的山路上,路过一个窄小而老旧的隧道,洞口已用石块封死。
这里,是曾经的关角隧道。
武警官兵守护最早修建青藏铁路时留下的老关角隧道,有近40年之久。2014年,穿山而过的新隧道,用“高海拔最长里程”的宏伟纪录,直接缩短了列车在关角山上盘行的时间。
速度提升见证着时代飞跃。现在的官兵,从未忘却昔日前辈的奋斗精神。
“现在营区没有什么是旧的,但在以前的中队,没有什么是新的……”在老关角隧道守了4年的老兵代鹏回忆说,“以前,我们房间的线路不能动,因为老化严重,一动就会掉皮,特别危险;院子里的墙也从不刷新,防止松动的砖块砸下来。”
冬天,他们会走入隧道,清理被狂风吹进洞口的积雪。有时,水滴会从岩洞上方落下来,打在身上。而这些矿物质超标的隧道水,也会流进官兵身体里。直到搬进新关角营区,他们才喝上了净化水。
老隧道长5000多米,官兵们每天翻过关角山,往返10余公里,从一端走到另一端巡逻。稀薄的氧气拖拽着脚步,在厚重的积雪上,每落下一个足印,就伴随着一次深呼吸。踩过一块块湿滑的石头,代鹏和战友们到达隧道另一端,认真巡查过后,又向着来时的方向行进。日复一日,他们走过这条路,也护卫着这条路。
除了武警中队官兵,还有一群老兵和关角隧道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2017年,中士王国盛回到青海老家探亲,偶遇当年修建老关角隧道的铁道兵郭仲安。
当王国盛提到自己在关角山当兵,老人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王国盛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紧接着,老人声音颤抖起来:“那个隧道,就是我们修的!没命名之前,我们都叫它‘二郎洞’。”
老关角隧道是老一辈铁道兵用血汗建成的。老人告诉王国盛,以前没有机械,全靠人工。他们用锤子加铁钎一点点凿山,每人每天砸一筐石头。施工过程中,随时会有山体塌方的危险。
“有天中午,我的班长进到洞里,来换我去吃饭。我刚走出洞口没几步,身后就传来了一声巨响……”年过花甲的老兵紧紧握着王国盛的手,一遍遍嘱托:“请你们一定要把它守好,那里有我的战友……”
后来,王国盛休完假回到中队,递交了选晋士官的申请。“我们守隧道,总比他们修隧道容易一些。如果守不好,有愧于那些老铁道兵。”他说。
直到现在,仍时常有老铁道兵回到关角隧道。2012年,上士左智站哨时,有位老兵赠给他一枚铜质铁道兵纪念章,他一直珍藏着。
对这群武警官兵而言,他们守护的,不仅是这条铁路承载的美好未来,也是前人奋力拼搏的成果。新老关角的精神,在他们身上传承,熠熠闪光。
汽笛响起,列车飞驰,守护着天路,也是在守护着幸福
九月,是分别的时节。高原的铁路带着少年的青涩来到军营,又在离开时载起老兵悠长的怀念。一辆辆列车奔向远方,最终抵达人生的不同站点。
退伍老兵离队后,通常会坐上火车去西宁。看到快经过关角隧道,老兵就发一条短信给战友们告别。于是,中队官兵提前来到铁道旁,站成一排,目送载着战友的列车离去。
车内,老兵远远望着日夜坚守的营区。列车渐渐靠近,他们只来得及最后看一眼列队的战友们,就被拉入深邃的洞口。
曾经,他穿过这段漫长的隧道来到中队;此刻,他又用同样20多分钟的黑暗穿行,向自己的军旅生涯告别。
当重见光亮的那刻,关角山的故事已经刻进老兵的生命,成了一辈子难以忘怀的记忆。
关角山带给所有人成长。年轻的官兵从这里出发,抵达更好的未来。
廖重权出生在四川达州,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他报名参军,就是想做些有意义的事。尽管守隧道的日子和想象中的军旅生活不一样,但他说,“只要是值得做的事,我就要做好。”
除了认真站好每一班哨,刻苦训练,廖重权还拿起了书本。“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学点东西。”他从未感觉到关角山有多么寂寞。
再过不久,已经提干的廖重权就要前往乌鲁木齐读军校。他会坐着眼前的火车去上学,毕业后也会经由同一条铁路回到这里。关于未来,他说:“无论在什么岗位,只要能释放出自己的能量,那就值得。”
铁路联系着个人命运,也关乎国家发展。多年坚守在关角隧道两端,通过飞驰的列车,官兵们也感受着时代的变化。
“这两年,铁路快递专列明显变多了。”廖重权说。
国家互联网高速发展,交通物流日益繁忙,提速后的列车满载货物,沿着昆仑山一路抵达高原藏区。数据表明,青藏铁路通车以来,沿线地区的经济增速逐年提高。
在这条高原“生命线”上,关角隧道守护中队的官兵每时每刻坚守战位。遏止破坏、隧道内营救、泥石流抢险……他们在汽笛响起前排除所有危险和隐患,只为目送列车平稳通过。
在关角山之外,还有昆仑山、开心岭、沱沱河……
武警官兵挺立着,身旁的青藏铁路穿过高原,伸向远方。
汽笛响起,列车飞驰而过。他们守护着天路,也守护着幸福。
(采访中得到张雅芳、李传龙、邱国振、傅乐意、张宾、王兵强、李振朝、岳亮亮等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用热血温暖荒凉
九月,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大部分地区刚送走酷暑的灼热,秋风乍起,寒生露凝。
对于守护在青藏高原天路旁的武警官兵,九月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短短3个月的夏天结束了,漫长的冬季拉开序幕;意味着窗外的草又要黄了,至少要等到来年六月才能再见绿色;意味着随时可能大雪封山,要做好物资和补给中断的准备……
站在海拔3380米的关角隧道哨卡,士兵张立峰眼神凝峻。他想起3年前的这个时节,自己被一辆军车拉到关角山。从“江北水城”到“登天的梯”,18岁“不恋家”的“狂妄”,被高原大风吹得不见踪影。3年来,每日守着脚下的铁路,他一次次目送来往的列车和车里欢笑的人们。
海拔4868米的昆仑山隧道旁,士兵王赏坐在温室里,享受午后的阳光。在他身后,“云端哨卡”巍然矗立,青藏铁路在“世界屋脊”蜿蜒而行。自从双脚因救人而冻伤,昆仑山的冬天仿佛更冷了。气温很快会降到-30 ,那时站立和行走都像踩在刀锋上。他摩挲着双腿,想要抓住冬日来临前最后的温暖。
海拔4650米的长江源特大桥边,匆匆吃过午饭,全副武装的唐兵和战友们开始巡逻。这是他行走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第11年。习惯了每日往返300多公里,也习惯了与藏羚羊为伍,他熟知这片土地的每一条脉络。在无边的荒原上,仅凭一小片水泊,他就能辨认方位。
这些驻守高原、守护天路的武警官兵,年少的不过18岁,笑起来眉眼弯弯,神色中还流露出几许天真;年长者已经在这里待了14年,这几乎是一个人青春芳华的全部。凹陷的指甲、皲裂的双手和后退的发际线,是高原留给这群年轻官兵的深刻纪念。
当被问是否会感到寂寞时,士兵县琪斌沉默良久。他常年红肿的脸上露出一丝落寞:“想家的时候,就去外面站着,看看远处,天空慢慢就亮了。”
过去8年,不知有多少个深夜,这位老兵站在黑暗中,凝望着远方无垠的旷野,凝望着和家乡同样的一轮月亮。
更多官兵的答案是:“习惯了。”
他们,习惯了高海拔地区每一次呼吸伴随的不适感;习惯了经年风雪在肌肤上刻下岁月的痕迹;习惯了窗外一成不变的景象;习惯了“白日与牛羊为伍,夜晚同星辉做伴”;习惯了远离烟火、无人倾诉的孤寂……
于是,用青春拥抱寂寞,成为一种习惯。于是,高原的荒凉,被热血暖热。
在黑暗尽头的光里,我们会再次遇见那群哨兵……
图片摄影:王金兴、杨 浩、彭 涛